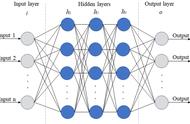(明)文徵明,寒林钟馗图。
文徵明和他的儿子文彭,确立了明代印人“文人化”身份,文彭还在印章中引入石材,文人不需要工匠帮助而可以直接独立完成。周应愿在《印说》中曾列举许初“篆印手镌,仿佛文博士”,陈淳、王榖祥“俱善篆”,张凤翼自篆“张伯起”三字白文印,又有王元微、王少微、许仍野、詹正叔诸人善刻者,足见当时文人和刻工多有合作或文人自己完成,风气极盛。
随着工匠社会地位的提高,关于工艺和名匠的记载越来越多,其中包括许多雕刻及刻工的记载,刻工事迹、姓名的记录也更加详细。明代中期以来的著名刻手如章简甫、章藻、吴鼎、吴应祈、吴士端、吴之骥、章镛、吴桢等人,其中以章简甫影响最大。王世贞曾作《章筼谷墓志铭》对其评价甚高,称其“能夺古人精魄”,孙鑛《书画跋跋》赞其为“迩来第一高手,尤精摹拓”。这一时期刻帖风气的兴盛,与刻工和文人的合作密切相关。

《文徵明、文彭父子致无锡华世祯信札》手卷
在明代有关印章的论著中,开始把印人和雕刻工匠进行对比。周应愿《印说》中提到嘉靖、隆庆、万历前期的“雕刻技人”:
至文待诏父子,始辟印源,白登秦汉,朱压宋元,嗣是雕刻技人如鲍天成、李文甫辈,依样临摹,靡不逼古。
鲍天成,吴县人,能雕琢犀象、香料、紫坛图匣、香盒、扇坠、簪纽之类,种种奇巧,迥迈前人。李文甫,金陵人,善雕刻花边,所镌花卉,皆玲珑有致。李文甫即是和文彭“合作”印章的名匠。即使是一些雕刻的好手,他们的作品也与文人的印章差异很大。这里,周应愿肯定文氏父子“始辟”文人印章的贡献,白文取法秦汉印,朱文在宋元印基础上而有发展,而批评雕工只能“依样临摹”,不能达到古意。这是由于工匠没有文化素养所决定的。工匠不能表达文人用意,刊刻也多讹误,《印说》又载:
玉人不识篆,往往不得笔意,古法顿亡,所以反不如石,石刀易入,展舒随我。小则指力,大则腕力,惟其所之,无不如意,若笔陈然,所以反胜玉。
雕玉工人不识篆书,不能了解书法笔意,因此不能表达“古法”,这种工匠的创作,“古法顿亡”,不是文人寄情抒怀的方式,而文人在石上刊刻能“展抒随我”,“若笔陈然”,则才进入艺术创作的状态。对大部分工匠而言,刊刻印章仅为工匠糊口之用。周亮工《印人传》载:
梁溪邹督学
(迪光)
曰:今之人帖括不售,农贾不验,无所糊口,而又不能课声诗、作绘事,则托于印章以为业者十而又九。今之人不能辨古帖、识周秦彝鼎而思列名博雅,则托于印章之好者亦十而又九。好者恃名而习者恃糈,好者以耳食,而习者以目论,至使一丁不识之夫,取象玉金珉,信手切割,又使一丁不识之夫椟而藏之,奉为天宝,可恨甚矣。
在印章普遍使用时,出现的情况是:不能读书者、不能作画者则“托于印章以为业”,不识名帖古器者亦“托于印章之好”,这使认为篆刻应该属于文人圈雅玩的文人感到痛恨,周亮工在《印人传》中引用这段话,也是对“一丁不识之夫”的大众都来以印获得“博雅”之名表示不满。明末张岱有感于工匠的文化品味低下,导致了“古法顿亡”,他以绘画上的唐寅和周臣为例,批评当时的这类人为“俗工”:
近世俗工,字皆杜撰,不足与语。余忆王太史之评唐寅、周臣画,谓二人稍落一笔,其妍丑立见。或问臣画何以不如伯虎?太史曰:“但少伯虎胸中数千卷书耳。”今兰渚之与俗工,其妍丑相去,确确由此。叮嘱诸人,其再读十年书,方可与兰渚语痛痒也。
既然工匠之印有文化品味的缺失,不能“入古”,但如果工匠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品味,或工匠通过与文人的交往、沟通,领悟到文人的志趣,与文人合作,是否可能不入俗格?或文人通过学习工匠熟练的技能,掌握了印章刊刻的基本技法后,能否使印章从“工艺性”走向文人化?作为“工艺品”的印章与作为文人雅玩的印章如何分野?
明代人已经开始提出“文人家印”这一概念来区分其他的印章。《印说》中云:“文人家印如屈注天潢,倒流沧海。”这种讨论主要突出了印章的人格象征意义,然尚未切入印章审美的主体。到了朱简时,这种讨论更加明确。朱简《印经》中将印章分为“工人印”和“文人印”:
工人之印以法论,章字毕具,方入能品;文人之印以趣胜,天趣流动,超然上乘。若既无法,又无逸趣,奚文,奚其文?工人无法,又不足言矣。

朱简所著《印经》。
这表明明代印人开始有了自觉的审美意识,文人之印以“趣”而突破工人之印以“法”来讨论印章的艺术表现力,这是对印章认识的突破,更是对印人认识的突破,这在印章从工匠化走向文人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金陵文化圈与文人印的形成
除苏州一地外,南京也是文人印章的策源地,《印人传》的写作正是在明代以来的金陵文化环境中完成的。嘉靖中期以来,文人士大夫跃升为金陵文化界的主流,这正是被称为“金陵之初盛”的时候:
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指为乐土。……嘉靖中年朱子价
(曰藩)
,何元朗
(良俊)
为寓公,金在衡
(銮)
、盛仲交
(时泰)
为地主,皇甫子循
(汸)
、黄淳父
(姬水)
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姘翠。此金陵之初盛也。
这批金陵文化圈的主导人物中,朱曰藩为江苏宝应人,何良俊为华亭人,皇甫汸与黄姬水为苏州人。这几个金陵以外的地区,以苏州文化最盛,对金陵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最重要。到了万历初年,金陵文化再度兴起:
万历初年,陈宁乡芹
(子野)
,解祖石城,卜居笛步,置驿邀兵,复修青溪之社,于是在衡
(金銮)
、仲交
(盛时泰)
以旧老而莅盟,幼子、百榖
(王稺登)
,以胜流而至止。厥后轩车纷逮,唱和频烦
(繁)
。虽词章未娴大雅,而盘游无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

朱曰藩,草书,次韵何元朗罢官诗,扇页,泥金纸本。
万历二十年
(1592)
后,金陵文化发展到“极盛”的地步:
其后二十年,闽人曹学佺能始回翔棘寺,游宴冶城,宾朋过从,名胜延眺,缙绅则臧晋叔
(懋循)
、陈德远
(邦瞻)
为眉目,布衣则吴非熊
(兆)
、吴允兆
(梦旸)
、柳陈父
(应方)
、盛太古
(鸣世)
为领袖。台城怀古,爰为凭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伤离之作。笔墨横飞,篇帙腾涌。此金陵之极盛也。
金陵文化从嘉靖中期到万历二十年,经过初盛、再盛到极盛的变化,确立了一种特有的文人品味,凭借其文化中心的地位而辐射到各地。
在金陵文化的发展、兴盛中,诗文、书画、印章、工艺等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如书法发展中篆书一体从乔宇、景旸、徐霖、陈沂到刑一凤、许初等书家一线相传,其中徐霖、刑一凤、许初等文人曾参与了南京地区的文人印章活动,并影响到吴良止、董玉溪、何震、吴鲁南等印人。因而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所反映出的文人品味在印人身上也得到鲜明的反映。周亮工在《印人传》中对印人生活、交游、雅玩的记录以及印人所体现出的文人品味也与金陵文化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
明代中期以后,
印章的“文人品味”是如何形成的?
在印章“文人品味”的形成过程中,印章材料的变革和自身功能的变化也值得特别注意。篆刻之所以向艺术方向转化,石质的印材是一个重大转变。
过去篆刻家和刻工分工合作,篆刻家写印稿,由刻工雕刻完成。这种普遍的方法到文彭时还在使用。随着石质材料越来越多地被文人采用,原先和他合作的刻工李文甫等仅仅是帮其镌刻牙章,而石质印材则更多地是由自己来独立完成创作。这样,印章开始和书法、绘画一样,完全成为文人“私人化”的遣兴物品。
石章虽从元代王冕时期就已被文人运用,但较为普遍的运用却在明代中后期。随着这种易被文人驾驭的印材运用,印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中国印章史也由此而转变为文人篆刻的历史,确立了“印人”的中心地位,正如傅抱石先生所说:
到了明末,便象绘画的艺术一样,发展的途径不止一端。因而此后的历史,不仅可说是私印的石印的天下,而且是以印人为中心的了。
印章的材料在艺术表现中,材料本身的好坏并不是欣赏的关键,关键是文人价值品味的确立。印材带有工艺性质,它所体现的是“做工”层面的美感,而光以材料而获得美感不是文人的追求。文人希冀通过自篆自刻,玩石弄刀,完成文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宴游吟唱、写字作画一样,成为文人自我修养的一个组成部分。
印章的用途,除了封泥为古代印章的主要用途外,其他用途有六种:一、物勒工名;二、器物名称的图记;三、战国金币上的印迹用玺印盖成;四、专作佩带之用;五、殉葬用印;六、烙马印。这七种用途多与凭信有关。而印章的凭信特性是通过其用途表现出来的,其用途在实用中的转化也必然导致印章特性的转化,还有三个用途:一、用于装饰;二、兼有商标功能;三、用于纪年。
明代中期以来,随着书画、工艺品的发展和大量印材的开掘,印章已和其他的文房用品一样,走进书斋,除了用于文人的书画创作、鉴藏等活动外,对文人而言,印章本身还具有了充分的“娱乐”和“雅玩”功能,这是不应忽视的。正是这种“娱乐”和“雅玩”功能的出现,使得印面的刊刻文人妙语、别称、戏语以及印章的风格、取法,印纽的制作工艺等也都成为文人雅集中品评、赏玩的普遍话题。
编辑丨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