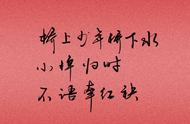晓渔兄:
上次回函时还能讲述日常散步的所见所闻,这些时日只能躲在空调房内“独抒己见”了。真是个烈日灼人的苦夏时分!酷暑难当,连读书都没法安放那份焦躁。适宜出门游荡的日子里,又因疫情而没法出门远足;“烈日炎炎似火烧”的酷夏时分,想出游又得有点不惧被烤的勇气。世事添乱,让人活在悖论之中。
不过正如兄之所言,“日课”成为安放日常的善剂良药,日记是我重整自身的日常练习。回想大学毕业后写下的十多年日记,似乎有点像陈子展撰写日记的跌宕感受:其曾在五四运动之后写下六七年日记,但因埋头粉笔堆中而陷于日常牢*;北伐革命令其为之一振,又因迅即而来的形势大变,怒将日记付诸丙丁,悲愤作诗以诉:“日记千言自此休,悔将椽笔写闲愁。腐儒事业一锅面,看汝糊涂到白头。”(引自廖太燕《私史微观: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的多元透视》)

《私史微观: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的多元透视》,廖太燕著,凤凰出版社,2022年6月。
不过,如今早已脱离了当年那份“高级趣味”。睡前打开日记,仅有流水账时便感不安,警醒自己今日庸碌,既缺乏与他人激动的交谈,也没能好好看上几页书写点感想,更没有对所见所闻进行些许日常性的思考练习。于今而言,日记更多的是督促己身每日当“有所为”,尽管隐约甚至明显地有着“隐身听众”的存在,同样督促着我巨细靡遗地“长篇大论”。
那些日常写下的连篇琐碎,或许也可称为我笔下的“昨日的世界”,也为我提供了怀旧的材料。正如兄所言,怀旧究竟是对过去的召唤,还是对当下的疏离;它究竟是情感的冒险,还是精神的密谋,实在难以厘清。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个人蜜尝的心灵毒药,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的“二手时间”:在1917年革命之前,亚历山大·格林就曾写道:“不知怎么,未来并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那个“我的时代结束得比我的生命早”的“二手时代”里,人们被迫地擅长把自己修剪成“室内盆栽植物”:“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过着封闭的生活,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只过自己的日子,不去注意四周,不去管窗外的事情”,很多事情仿如海市蜃楼,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它只能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
较之于全书那些对往昔或当下充满抱怨的故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当属全书末尾那则最简短的故事:当邮递员推开俄罗斯乡下的篱笆门,将苏联解体的消息告诉乡下老妇人时,她说:“在我们这里,过去怎样生活,现在还怎样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回事。几十年来我都只关心那些生活必需品,人们说什么,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她来说,世界依然是那般模样,在这震撼世界的时代板荡中,她似乎什么都没有失去。姓资姓社等时代大事,似乎跟她没什么关系,“反正要等到春天才能种土豆”。除了春天的如期而至,那位老妇人的日常生活,不必较量昨日与明天,也不必琢磨绝望与希望;时代是悲是喜都无甚关系,她如同乡土世界里那些风餐露宿的年老大树,来年的风吹来,又可以安然地吐蕊绽芽。

《二手时间》,[白俄] 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当然还有一类活法,更像是刘文瑾在《道德崩溃与现代性危机》中所谈到的那样,既融合了某种难以理解的“崇拜”,又吸收了那些理直气壮的“市侩”;既能献身于非功利化的狂热,也能追求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既能够对远方输出频繁不绝的激情,也能够对眼前采取干脆利落的冷漠;既能对虚假空洞的概念保持抽象的激情,也能对真切存在的现实坚守厌倦的冷漠。这是一种没有拥有“小我”却能拥抱“大我”的悖论式生活方式。在该书的第二章,刘文瑾书写了捷克现象学家扬·帕托什卡同样的描述,这两种大小之“我”自行剥离了“关怀灵魂”(Care of Soul),由厌倦(I’ennui)和迷狂(I’orgiasme)酿造着新的生活方式,维护着一种“日的统治”(Rule of Day)。在某种程度上,厌倦指向了意义的消失和自我的抛弃,而迷狂携带着宗教般的献祭。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沉睡的人各自生活在各自的世界,只有清醒的人才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如何让你我之间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即使远在天边也能近在眼前,而非即使近在眼前也如远在天边,终究还得回到“意义”这两个字上。尽管这两个字让人疲惫不堪,但能将我们从泥淖中打捞出来,至少能让我们下坠得不那么过分的迅速。就像刘文瑾在书中所写:“恶之平庸”其实是提醒人们:与其说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艾希曼,不如说人人都“有责任”避免成为艾希曼。无论是对过去的怀旧,还是对未来的想象,“时间的种子”只能奠基于正确的当下,来自于自我能够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判断与责任。
突然翻出这部去年出版的书来阅读,主要还是为了解救和警醒自身的困境,生怕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了轻易宽恕自我的能力;在新闻疲惫之后陷入玩世不恭的偶尔作弊之中,尽量避免让自己成为“生活中的艾希曼”。各种原因导致的无法远足,还有灼*世人的当头烈日,让困在空调房里的我似乎逐步失去了某种共同感的生活经验,徒陷于某种略感心安的虚空之中。这种日常的心安,偶然回瞥之间,很容易逆转成扎实的不安。

《道德崩溃与现代性危机:三位“后奥斯维辛”思想家的遗产》,刘文瑾著,思想与社会丨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3月。
每每不安之际,哲学理论很难将我打捞出来,在深居简出读闲书而缺乏共同经验的日子里,依然还是更愿意选择文学类作品来与内心进行对话,仿如远方的某人宽慰着精神的困境。在前几天被高音喇叭吵醒叫嚣下楼排队做核酸时,让我想起了寒天雪地里的漫长队伍——奥尔加·格鲁辛的《排队》。
在《排队》里,大变化三十七周年之际,安娜下班后换了一条路回家,竟然自己陷入了一场长达一年之久的排队马拉松。尽管起初谁也不知队伍的尽头究竟售卖的是什么,但在精神匮乏、物质短缺的灰暗年代里,突然传来一份即便遥不可及的希望,却成了跨越冬春夏秋的日常美好,哪怕它徒劳无功,即便它虚无缥缈。“他们不时可以抱着一种毫无顾忌、直截了当的迫切感依赖另一人,在饱含雪意的黑暗的天空下,在恐惧、希望和信任之下相互团结,就像跟家人那样说话,或许,甚至他们都不会这样跟家人说话。”尽管,他们在漫长的春夏秋冬中苦苦等待的东西,“那真的不属于这个世界,尽管它理应属于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
当然,这是我排队后阅读《排队》后的感受。作者将斯特拉文斯基受邀回苏联的音乐会门票预售故事改编成了这么一部小说,更多着力于匮乏的人们因排队而打乱生活节奏,彼此之间却也在排队过程中由陌异到熟悉而建立了新的生活秩序,以“等待戈多”开端,由“安琪礼物”收尾。作者的出发点和我的阅后感,形成强烈反差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我们“没有遮遮掩掩的秘密”;而安娜不知她们排队能买什么,但排队的“希望”能够撩动她们的*动之心,队伍的尽头是远方——别处的生活或早已消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