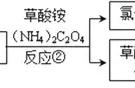□哈 米
文化是什么?
词典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别是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我说,文化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
没有灵魂,个人、集体无异于行尸走肉。
文化似水。
水看似小鸟依人般温柔,把它盛在啥形状的容器里它就听话地成为啥形状,方的,圆的,三角形的,随意。
文化似水。
水无孔不入,柔顺地抚慰、洗涤、拯救你的灵魂,修复你被弄残的大脑,让你变得睿智、善良、磊落、高尚。
文化似水。
砍不断,砸不烂,一旦聚成洪涛汹涌怒吼起来任何都无法阻挡;因此被用来与革命相类比……
刘心武曾通过他被誉为“里程碑式”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塑造了两个非常接地气的人物:团支部*姑娘谢惠敏和小流氓插班生宋宝琦。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形象,其实同样都是“脑疾”患者——前者病毒入脑;后者压根儿脑壳空空如也。刘心武没有明确开出药方,但整篇故事呼喊着:文化回归,刻不容缓!尽管小说尚欠精巧,可40年后读来仍觉没有过时。

《班主任》 刘心武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如何深入地论述文化的作用?我不是理论家;只是个读书不多的读者。只好凭借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里三个纳粹德国人的行为来做个注脚,表达一丁点儿感受,对与不对,但求方家指正。
《巴黎烧了吗?》:肖尔铁茨
先说纳粹将军肖尔铁茨。
我难忘这部书:《巴黎烧了吗?》(美国记者拉莱·科林斯和法国记者多米尼克·拉皮埃尔的纪实报告与阿兰德龙和贝尔蒙多等大明星们联袂主演的同名电影)
它逼真、详尽、鲜活地记述了1945年法兰西人民和盟军保卫巴黎抵抗纳粹的英勇斗争。
“巴黎烧了吗?”是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那天,希特勒对他下属约德尔上将狂吼着的责问。

[美]拉莱·科林斯 [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译者:董乐山 译林出版社
用这句话作为标题的这本书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情节:
巴黎莫里斯饭店德国司令官冯·肖尔铁茨将军办公室的阳台。
肖尔铁茨是奉希特勒密令前往坐镇巴黎,一旦巴黎被盟军攻克,他就立马把巴黎炸为一片废墟。全城各个要害部门都已深埋了重磅炸药,只待将军一声令下,全城倾刻化为平地。
这可急坏了巴黎市长泰丁格。他在肖尔铁茨办公室面街的阳台上,对这位亲手掌握着炸弹引线的大巴黎司令将军苦口婆心:
“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的建筑。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们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肖尔铁茨沉默片刻,说:“你不愧是巴黎的杰出辩护士,你完成了你的任务。而我,作为德国将军,也同样要完成我的任务。”(《巴黎烧了吗?》P.95)
后来,在同一阳台上,前来劝说肖尔铁茨别毁坏巴黎的中立国瑞典的总领事拉奥尔·诺德林,听到俯望街景的肖将军对他身边的人说:“我喜欢这些漂亮的巴黎女人,把她们*掉,毁灭她们的城市,会是一场悲剧。”
诺德林趁机严肃警告肖尔铁茨,夷平巴黎,他就会犯下一桩历史永远不会宽恕的罪行。肖尔铁茨仍回答:“我是个军人。我奉命行事。”可内心已经动摇了,他不想让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
终于,肖尔铁茨俯下身来,非常严肃地一字一顿地告诉这位瑞典外交官:唯一可以阻止执行“扫平”命令的是:“盟军迅速抵达巴黎!”(《巴黎烧了吗?》P.203)
肖尔铁茨竟然冒着“叛国罪”具体帮助诺德林越过封锁线,去向盟军报信,让盟军及时进城保住了巴黎。
重述完这个场景我想就无须再多嘴了吧!
《沉静的海》:凡尔奈
如果说《巴黎烧了吗?》是气势澎湃的交响乐,那么维尔高1942年出版的小说《沉静如海》(小说译名《海的沉默》)堪称一支哀婉美丽的小夜曲。
1949年据此拍摄的同名黑白片,跟小说一样,在极其简约、舒缓的描述中,体现出内涵的凝重和隽永。我非常喜欢这小说和电影。通常情况是重拍片往往不如原片,没想到2004年由皮埃尔·布特龙重拍的同名彩色片,却极大程度上拓展了小说和原片的情节,丰富了内涵,堪称一首在灿烂文化浸润下的银幕战争抒情诗。

《沉静如海》1949年版黑白片
影片描述二战时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有一人家,只剩下一老人和他年轻侄女相依为命。一天,他们的一个房间被占领军征用了,供一名德军上尉军官凡尔奈·封·艾勃雷内克居住。他原本是位作曲家,他信仰希特勒,但景仰迷恋法兰西灿烂文化。高雅文化熏陶成的气质,促使他以平等、友善、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自己占领地的居民。
但一老一少的房主出于家仇国恨,自然对这位入侵的不速之客报以冷漠和敌意。尽管早出晚归的上尉军官进进出出始终行礼问候,自言自语地赞美法兰西的美好,老人和少女(2004版的电影是爷爷和孙女)。始终以沉默相对。德军军官所有有感而发的言语似乎都是朝着沉静的大海在倾诉。日复一日,军官态度始终如一。大海依然沉默。但海底深处潜藏的热浪在翻腾:少女与上尉相互萌生出了读者和观众不易觉察的变化。可这是一种纯净而无望,真情又荒唐,无力抗拒又没法接纳,与国仇家恨相违背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