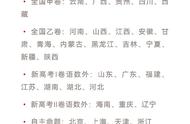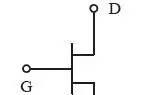在曾经的出租屋,刘颖用心塑造自己的生活。为了舒服地泡澡,她还买了充气浴缸。受访者供图
虽然价格便宜,但舍友对卫生标准要求不同,公共区域的杂乱肮脏令她难以忍受。租户们的生活作息也有错位,刘颖常因隔壁的噪音失眠,争抢卫生间的情况也时常发生。放弃群租房后,她开始租住有独立卫生间的一居室。
独居女性这个身份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朝阳区某小区租房时,因为快递员常直接把她买的生鲜冷冻食物放在自提柜,和快递员沟通无果后,她打了投诉电话。本以为事情可以解决,但晚上回家后,刘颖发现家里的锁眼被堵了,门口墙上贴着性服务的小广告上,也被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门口没有摄像头,我也没有证据确认是他,只能吃哑巴亏,装作不知道这件事。”刘颖说。
怕被继续报复,刘颖只能压制着自己的愤怒,在与快递员相处时保持和颜悦色。去年10月,房子到期后,房东因决定卖房没有续租,本就战战兢兢继续租住的刘颖又迎来突然的变动,她被限制在两天内搬离出租屋。
匆忙地收拾行李,把行李寄放在朋友的工作室后,刘颖带着随身物品住进了公司附近的酒店。她本以为住在酒店只是过渡期的无奈之举,却没想到打开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之前租住在朝阳区5500元左右的房租相比,长租酒店每月的费用不超过4500元,还包括了打扫房间,补充矿泉水、卫生纸等日用品的支出。
刘颖关注的安全问题也有了更切实的保障,酒店的住户和访客都需要刷身份证和登记,有24小时的安保。点外卖、收快递时只用填写酒店的地址,前台会帮忙代收,再由机器人送上门。住在酒店,刘颖感到安心,她觉得自己开始掌握对生活的主导权,不会再被*扰或者被驱赶,她有选择离开或留下的权力。
从她生活中剥离的,还有别的东西。刘颖形容自己是典型的巨蟹座女生,习惯付出,不求回报,总是不自觉把照顾身边人当作自己的责任。18岁后,她实现了经济独立,没有再向家庭索要生活费。刘颖毕业于长沙一所大学的传媒学院,从大二开始,她在湖南卫视、央视等大平台实习积攒工作经验,同时也接一些编导、拍摄的零工,在艺考的培训机构兼职。努力工作攒钱的那个时期,刘颖说,“钱是我的安全感”。
用几年努力积攒起来的安全感,被接二连三的震动打碎。在大学期间谈的一场恋爱里,刘颖习惯性地为男友付出,“把所有挣的钱都给他了”。男友嗜赌,刘颖消耗在这段关系里,付出财力和精力,想要“把男友拉回正道”。当男友又一次问她要钱,她实在拿不出来时,男友愤怒地摔掉了手机,“把我摔醒了,这才下决心分手。”刘颖说。
结束这段亲密关系后,她过上了一段安心攒钱的日子,又再度被拖入泥沼。在安徽蚌埠,刘颖的妈妈在网上参与不正规的小额贷款,欠的钱越滚越多,刘颖只能顶着压力帮母亲还钱,最多时每个月需要还5万元。这对一个在读大学的学生来说不是小数目,刘颖无奈,也觉得委屈,“好像我辛苦挣这么多钱都没有给过自己。”
用攒钱铺就的安全感道路,在经历了互联网借贷平台的爆雷后终于瓦解。2018年,工作两年后,刘颖攒了30万元准备在老家买套小型公寓。房子都看好后,自己分散在各个平台的钱却再也拿不回来了。“努力就会有回报”,这个支撑着自己的信念开始动摇。此后的4年,刘颖用松弛治愈着曾经的失去,不再像过去一样相信努力和赚钱的意义。租房不顺利后,她住进了酒店,暂停了所有工作,“好像人生目标变了,我可能不太想要有钱,不想再顾着我男朋友或者是家人。我想先顾好我自己。”
决定照顾自己感受的刘颖居住在酒店已经超过了半年。被问到打算在酒店住多久时,刘颖回答:“只要价格控制在5000元以内,我会一直住下去,价格低、安全、有阿姨打扫卫生,没理由不住。”

在酒店的大多时间,刘颖躺在床上玩手机。床头柜上放着两瓶酒店提供的免费矿泉水和卷纸。新京报记者 徐雪飞 摄
对35岁的小北来说,长租酒店同样也是对既定生活轨迹的一次逃离。独自一人在香港居住16年,小北说,“这十多年都在沿着按部就班的生活步调向前走。在酒店长住,终于有了一种游离在生活之外的架空感。”
在此之前,生活是一条坚固开阔的大道,她要做的,是相信它,并且坚定地走下去。2006年,小北以河南某市状元的高考成绩考入香港大学。成长于小城市的女孩通过高考的独木桥来到香港,毕业后,又顺利地找到了当地一家媒体的工作。
顺遂是故事的A面,故事的B面,是一个小城女孩多年在文化冲击下难解的困惑不安。小北回忆起入学的迎新会上,社团的学姐学长们看到她后主动把语言切换为普通话,她很好奇,问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从内地来的。不出几日,她明白了问题的答案。香港本地同学身上或多或少带着精英学生的印记:英语好,打扮时髦,身上有可辨识的轻盈和自信,在人群中显得突出。相比之下,自己打扮土气,第一次接触全英授课,脱离不了笨拙感,与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班里的大陆学生,也大多来自北上广,毕业于国际学校。在大学校园里,小北说自己处在边缘,同学们的自信和眼界之宽广,让她羡慕,也让她自卑。
这种紧绷感一直延续到工作后。刚毕业的第一年,像多数同学一样,小北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行走在西环的路上吃饭、买东西,在摩肩接踵的人流里总会碰到同校的熟人。这让小北倍感压力,在并不融洽的群体里,身为外来者的她拒绝着来自熟人圈层的规训,强烈的自我意识驱使着她想要逃离。
2011年,在母亲的支持下,小北决定买房。“房子,是安全稳定的栖身之所,意味着结束漂泊,重获归属感。”怀着这样的念头,小北一个人看房,她看中了离岛区的大屿山,在这里,她可以远离市区和人群,似乎终于感到安全。
追求世俗标准的痛感
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教授杜素娟曾在采访中说道,“面对一些世俗标准不同的态度,社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很想达到世俗标准,认同而未达到之前所感到的痛苦;一种是怀疑现有的标准,当你拒绝规训时一定也会产生痛感,这个痛感表现成社恐。”小北和周芹都开玩笑地称自己为“社恐”,她们曾迎合过主流生活和标准,为此而努力,也因怀疑这套秩序而痛苦。
在香港,多数人以“上车”(买房)为固定的人生目标计划自己的人生:独立生存,存钱,买房,用余生还房贷。逃离了熟人圈层后,小北发觉自己掉进了另外一种主流秩序中,她需要为另一种世俗标准而努力:像大多数人一样务实,买房还贷,努力工作完成晋升,结婚生子。
居住在香港离岛区的大屿山,每天清晨9点,小北乘船去中环码头,在海浪的起伏中吃完早餐,再转地铁半个小时去香港市区的公司上班。晚上七点下班后,再坐船回家。
这样的生活悠闲,却也静止。当初买房时,小北看中的是离岛区的僻静,没有香港市区的拥挤和逼仄之感。居住在这所房子的十多年间,其他的朋友或结婚生子,或海外深造移民,只有她的生活留在原地。因为大龄未婚,和父母的矛盾也日渐激烈。她渐渐对这种生活产生了怀疑,在学校做最好的学生,在家庭里做父母的好女儿,在社会上努力做“精英”,“似乎大家都在向前走,只有我像游戏里的NPC,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的主题。”
2020年暴发的疫情加快了松动时刻的到来。封闭的生活让小北迫切地想要做一些改变。毕业后的十年间,小北换了三次工作,大量重复性事务和冗繁的合作关系消磨着工作的意义,工作不再能提供给她价值感。同时,在具体的生活中,她发现自己似乎失去了感官体验。在小北住所的窗外可以望到迪士尼,有时夜晚7点半,迪士尼城堡会在夜幕中亮起彩灯,璀璨的烟花一朵一朵炸开。从前,这些意料之外的烟花是生活的奖赏,渐渐地,小北发现岛上的海浪,雨水,花朵,甚至迪士尼的烟花,都不再让她有所感触。
房子安抚了外来人的漂泊之感,却也给她带来了新的禁锢。“好像在这个城市中,我生活中的选择更趋于保守。”雁小北说。
2020年的一个夜晚,小北在豆瓣上看到一位女性分享了在泰国的生活体验,在她的描述里,泰国人不太看重世俗标准和成功的*,压力不大,松弛快乐地在生活。像是突然触摸到另一种可能性,当下,小北打开电脑开始查阅,看到了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文化管理专业还在招硕士生,就立刻投递了申请。5月份,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小北辞职,把房子租出去,住进了酒店。
说起为什么会坚定地选择住在酒店,周芹想起自己小时候看过的一本书,名叫《拆掉思维的墙》。到现在,她仍能记得这本书里一句话:“从职业发展来看,一套房子毁灭一个梦想”。
周芹的梦想,是当一名“数字游民”,数字游民的核心特质之一,是工作不受地理条件和时间限制,但在此前提下可以选择性地去全世界不同地方生活。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挣脱刻板、规训和既定的藩篱。居住在酒店,过一种临时生活,在她看来是对梦想的保护,背着的黑色双肩包,带着电脑和耳机,她可以随时离开。
周芹期待的“游牧”式生活,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2018年,她从新闻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一家新媒体工作,日常工作内容是输出一些品牌新媒体文章,她称这份工作为“写软文的”。有时,安排的任务是写出看似新闻报道,但实际上写作方向是早已安排好的通稿。在新媒体营销中,洗稿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她需要在领导的授意下抄袭一些头部或者竞品公司的文章,领导告诉她,这是“拆分爆款”。
除了对工作内容抵触,周芹需要无条件服从公司的纪律规范。新媒体公司加班严重,但无论加班到多晚,公司要求员工每天必须在早上9点前上班打卡,迟到者会受到批评。公司内部,她面对的竞争者众多,“他们更年轻,学历好,工作能力也强”,她觉得焦虑,总担心自己被开除。在和领导的沟通中,领导也以打压式沟通为主。从校园走向社会,虽然周芹早已做好了“硬着陆”的准备,但这一次的工作经验和她未能成熟应对的“社会规则”还是让她感受到痛苦。
她会记得工作中领导的问话语气,在每天结束时反复琢磨其中蕴含的情绪。“这种觉得自己不被信任的感觉,像是我体内的木马程序,每当遇见事情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应激反应”。
“我觉得可能是你没有选择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比较惨的时候,会选择一些社会告诉你的正确做法。”带着这份失败感,周芹回到了老家河南安阳,开始同时准备考公和考研。双双失败后,2022年,周芹回到北京,决心调整自己,她开始居住在酒店,迈入“做自己”的艰难跋涉之路。

周芹长住在北京天坛东门地铁站附近的一家酒店,卫生间里没有周芹的私人用品,她使用大量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用品生活。新京报记者 杨柳 摄
一些新的可能性
2022年初,周芹回到了北京,在一家青年旅舍住下。在这里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年轻人入住,他们会在饭后讲述自己的故事,弹着吉他举行小型客厅的演奏会,会一起看全英文音乐剧《汉密尔顿》,相互推荐工作。周芹觉得自己在准备考研和考公期间放弃的,那些她最在意的东西又都回来了。
但青旅不可能一直住下去,高强度地暴露在社交环境令人疲惫,2022年4月,周芹搬去了更具个人空间的酒店。
2022年5月,北京疫情中,周芹成了密接人群,隔离结束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自己,她选择了一家均价在300元左右的快捷酒店。因为价格昂贵,第二天,她搬去了附近一晚只要150元的酒店。因为曾是“密接”的身份,她的房间被安排在了楼道的尽头,并且她被要求不能随意进出房间。
这是第一次,周芹意识到,住在酒店并不意味着“说走就走”的自由。拥有自由的幻境破碎后,非常偶然地,6月份,她刷到朋友的一条朋友圈,照片里,朋友养的猫咪慵懒地躺在一床被子上,被子是最普通的格子花纹。猫咪可爱,画面温馨,周芹在朋友圈下面评论:“好羡慕你有自己的被子。” 朋友回复她:“难道你没有自己的被子吗?”
身边的被子是酒店里一客一换、带着轻微消毒液味道的白色被子,周芹回复朋友,“我有,但那不是我的。”
像这样感受到孤独的时刻并不多。多数时候,周芹仍然享受在酒店里的日子,她仍然相信“游牧式”生活的可能性,在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她列了长长的读书观影清单,运营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她看来,生活的尽头不是考公或大厂,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变成真正的“数字游民”。
研究生的课程从8月下旬开始,从五月到八月,小北度过了人生中最“无所事事”的一段时期。在此前33年的人生中,小北尽力做一个“不给父母添麻烦,不游手好闲,能让父母认可”的女儿,不思进取是可耻的,因为满足而停止努力是不可取的,她鞭策着自己,在困局里失去了快乐。小北形容住酒店的日子像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觉得生活好像终于有了一些盼头,一些新的可能性,休息了很多,也对新生活展开很多计划。”
小北开始习惯自然醒,每天早上做三明治吃。中午在酒店附近闲逛的时候,正好是上班族茶休的时候,在办公楼下面,上班族们穿着正装,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抽烟,餐厅外面也排起了长队。因为赶时间,很多人只能打包外卖,即使有时间坐下吃饭,多数人都会点诸如烧味饭、牛腩面这些可以快速做好的食物。
小北一个人吃饭,经常和其他人拼桌,她能用余光看到身边人的手指不断地在手机上游走,在回复着各种消息。作为观察者,小北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她发觉自己拥有了太多奢侈的时间,“可以在任何时间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失去的知觉也在慢慢被找回。在酒店附近,小北最喜欢的一处是位于维港海滨的“油街实现”艺术空间。这座拥有红砖瓦顶的二级历史建筑有一座两层高的建筑作展览及活动用途,还有约3000平方米的户外空间,展示大型户外艺术装置。在这个“城市中的艺术绿洲”,小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午后。她最喜欢的是叫作Flow/汩汩的艺术装置,仍记得初看时的震荡:在一个宽阔的房间里,她坐在中间条凳上,入座后,房间变得完全黑暗,极度安静,前几分钟,小北觉得自己丧失了所有的感官,而后,内心的感受却渐渐明晰。突然之间,从房间黑暗的一头有一个闪亮的光点,一路穿行到了房间的另一头,接着另一个光点又出发,每个光点的路线都有所不同,光点也越来越多,但是它们都去往了同一个地方。

在香港“油街实现”艺术空间,小北度过一个又一个午后。受访者供图
“能感受到一种自我的渺小,一种世间万物的殊途同归。”小北说。这个展览,她看了好多遍。直到建筑外绿地的颜色从苍翠转为多彩,落英缤纷,是秋天了。在泰国完成学业后,小北回到香港,再度住进了自己的家,像艺术装置里的小光点一样,在短暂的偏离轨迹后,它仍飞去了那个与千万人相同的归途,属于她的大道。停下脚步的这些时间,曾经的疑问也没有得到解答,但至少,小北说,她开始承认自己的脆弱。她终于触摸到曾经初到香港时,自己艳羡的那种轻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