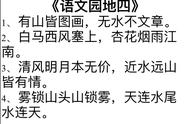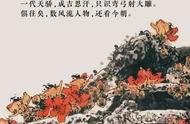每当春天来临,最不能触碰的是西湖。许多人说,一想到西湖,便止不住思念,思念谁呢?也许各不相同吧。只因西湖边自古以来发生了太多的故事,太多的爱恨情仇,总会牵动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苏轼触景生情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看来在苏先生心中,早已懂得了浓淡之辨证法,哪怕是错爱千年,总有挥之不去的情愫萦绕。
记得在福建工作时,唯一一次去武夷山就被朱熹的诗吸引了。朱先生与武夷山缘分不浅,常年在青山绿水间徜徉,诗兴大发是早晚的事。果然,朱熹写了一首长诗献给武夷山,至今仍被传唱。《九曲棹歌》开头便是“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这首280字长诗饱含浓情,写尽了武夷山之秀、奇、灵。可以说,武夷山因朱熹这位常客而文脉悠远,朱熹也因武夷山之灵秀而才思奔涌,一座山与一个人,成就了永久的诗意佳话。

诗人眼里见景
心中生情
若一不小心被他们写上一笔
那便仿佛成为社会肌体的
文化基因
久久流传于后世
我在苏州时专门去拜访寒山寺。只因了张继那首《枫桥夜泊》,红遍大江南北、也红遍时间长河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如今已是“寒山寺外姑苏城”。尽管城市在变大,但诗意仍然弥漫在这座城市的空气里。
老家安徽,也时常被诗意浸染着。别的不说,就那一汪“桃花潭水深千尺”,让多少游客不辞辛苦慕名而往。诗人已经远去,汪伦亦成记忆,但作为曾经的见证,桃花潭的水,至今还在人们心灵的深处荡漾着旷世友情、笑醉狂歌!

有人说,诗人总在江南乱了方寸,因为江南四季都是诗境。此话只对了一半。风沙漫漫的北方边塞,不只有荒野的苍凉,还有那奔涌的热血。“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君不见,那些意境苍莽雄阔的边塞诗,抒发了多少人心底的悲情离绪,又鼓荡起多少人胸中的英雄豪情?就拿黄河来说,众多诗篇因它而兴,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叹,就是大河催生的一份悲凉。
当然,诗词是时代的产物,“阳关”之外照样有“故人”的今天,这份悲凉早已消散在浩浩春风里。就像忻州雁门关外,金戈铁马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响,如今更多地发生着春天的故事。

我想无论古今,触景生情,妙笔生花,恐怕是很多诗人的共同经历,人与人同样会因诗而留下佳话。在福建工作时,一好友为现代诗人,某日相邀去福州近郊鼓岭游玩,登山时下起了毛毛细雨,在得知山中经常飘雨时,我脱口而出“山飘无常雨”,朋友立马对曰:“水映有晴天”。这两句即兴吟出的诗,记载了我俩的友谊。已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想来,仍历历在目。关于这段回忆,我来忻州工作以后,还时常提及,友人也十分感慨。
2
打开记忆的收藏夹,这些诗句中的地名不断浮现。我在想,诗中的远方是何等幸运,又是何等令人神往。因诗而出名,这些地方熠熠生辉起来。
我以为,这可能跟中国古代诗、歌不分家有关。流传至今的古典诗词,在当时都是可以和乐歌唱或者吟诵的。诗就是歌,歌就是诗。诗与歌就像一对孪生姐妹,从诞生之日起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它特有的声情韵律感染着万千读者,浸染着人们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