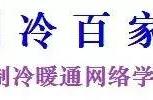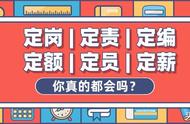几十年前来莫高窟的老一辈,有些已经辞世,按照他们的遗愿,他们的骨灰被安放在莫高窟对面的沙丘上。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摄
1935年,留学法国的青年画家常书鸿在旧书摊遇到《敦煌石窟图录》,回国、四处逃难,在八年后去了敦煌;1944年,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学生段文杰遇到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完成学业,在一年后来到莫高窟。从1947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洞窟里“面壁”,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窦占奎……
曾经的丝路重镇,在那时已经变成了边陲小城,被沙漠和戈壁包围着,日光炽烈。因为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擦脸、擦身、洗脚,用完还要留着派上其他用场;冬天睡觉前,把石头放到灶里烧热,然后用毛巾包起来,抱着取暖;夜里,为了看守骆驼和羊群,需要派人值班,拿着猎枪防狼;天亮后,用镜子和白纸当反光板,就这折射进洞窟的阳光临摹壁画、修复雕塑……
到现在,曾经的青年已经进入暮年,其中一些人已然辞世。二十余座黑色墓碑卧在沙丘上,隔着佛塔、戈壁、干枯的河道,和莫高窟对望。
“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对媒体说。
现在,帮助莫高窟对抗时间的接力棒被后辈的年轻人拿起来,在不同的时代走同一条路。
刚来的时候,俞天秀觉得山里的生活枯燥,叫上朋友去市区吃烧烤。返程时,一群年轻人心血来潮,决定走回莫高窟。一边嬉闹一边“寻宝”,从夜里十二点走到上午十一点。
许多年后他听闻,老前辈们当年走的就是那条路,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进城全靠步行,遇上急事才坐驴车或是牛车,路上还可能和狼对峙。
老一辈的莫高人没有太多选择,但对莫高窟的中生代而言,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机遇像洞窟一样密密麻麻地在眼前铺陈开来,年轻人有了更多元的工作选择,也有了更低成本的离开的机会。
和前辈们相比,这些年轻人身上少了历史气质,鲜少把“奉献”、“一切为了国家”挂在嘴边,更多关注个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讲解员陆佳瑜说:“这里工作待遇算不上优越,工作环境也不那么舒服,愿意留下来的,大多是热爱莫高窟的。人选择喜欢的职业,职业也在筛选适合它的人。”
入职第一年的元旦晚会上,陆佳瑜和同事们组了一个小乐队,编排了一个唱跳类节目。晚会结束后,她正在收拾东西,樊锦诗经过,年近耄耋的老人看着陆佳瑜笑:“年轻真好啊。”
和往常一样,樊锦诗穿着黑裤子,素色外套,笑起来弯着眼睛,皱纹从眼角和嘴角散开。陆佳瑜提出合影,樊锦诗乐呵呵地答应了。
陆佳瑜说,以前对樊锦诗的了解,大多通过电视和书本,以“敦煌的女儿”身份出现,朴实、伟大又崇高,在陆佳瑜心中是“至高无上的偶像”。她在带游客参观陈列馆时看到过樊锦诗年轻时的照片,“满脸的胶原蛋白”,但那个元旦,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樊锦诗,“发现她也是个普通人,脊背佝偻了,腿也弯了,显得很瘦小”。
当天晚上,想起那句“年轻真好”,陆佳瑜感慨了半天:“她也年轻过啊。”
作者简介
▼

王双兴
夜里写诗,白天做梦
E-mail:287843590@qq.com
洋葱话题
▼
你去过莫高窟吗?
后台回复关键词“洋葱君” ,加入读者群
推荐阅读

弑母疑凶吴谢宇的双面人生

砸碎安全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