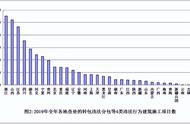——怀念父亲母亲
作者: 任永学
这一段小时候的往事让我怀念慈祥的父母双亲。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也就是八九岁的年龄, 一年的腊月,母亲去街道办事处开会了。家里铁锹头歪在院角的雪堆里。我盯着这根被磨得油亮的木柄,突然想起街坊邻居家的小朋友们那些油漆陀螺。菜刀在木头上划出深浅不一的刻痕时,虎口震得发麻,木屑雪花般簌簌落在棉鞋面上。
"哧啦——"父亲新打的锯子突然咬进木头,惊得我差点摔下板凳。铁锹把短了一截,断口处裸露出新鲜的木芯,像道流着松脂的伤口。钉图钉时太过用力,锤子砸在拇指上,含在嘴里的混着铁锈气。
冰河上的陀螺转出银亮的光圈,大兴和海泉他们围着我跺脚哈气。鞭梢抽破凝固的北风,木陀螺在冰面划出细密的年轮。
晚上爸爸下班回到家,蜡烛把父亲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缩在炕角,攥着尚带体温的陀螺,担心父亲的训斥和修理。他的手指抚过那些歪斜的刻痕,胡茬蹭在我额角:"这楔口要是再斜三分,转起来更稳当。"灶台飘来葱花饼的香气,母亲把铁锹头重新安回变短的木柄,雪地里的新豁口像咧开的嘴。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外孙要玩电光陀螺时,我仿佛又闻见七十年代的老松木香。冰河早化了,可那柄短了木把的铁锹,分明还在记忆里闪着温润的光。
江南窗外的玉兰开了。爸爸,妈妈,当年的木陀螺,在另一个世界转得可还稳当?父亲母亲你们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