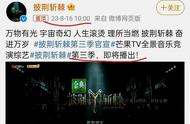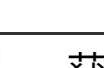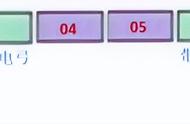《桶川跟踪狂*人事件》,[日]清水洁著,王华懋译,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版。
当然,客观来说,媒体自有其正面作用,1999年10月26日,年轻女子猪野诗织在日本埼玉县JR桶川站前遭人持刀刺死。受害者生前长期受到跟踪*扰,她多次向警方报案,警方却未予重视。最后因为警方的不作为,加上犯罪分子的蔑视法律,造成了年轻的女孩惨遭*害。如果不是记者清水洁不遗余力地跟踪调查,撰写了纪实性报道《桶川跟踪狂*人事件》揭露警方的失职与犯罪者的真面目,正义根本无从说起。
宫部美雪在小说里也提到一位高级警官在入行的时候经历过日本著名的“三亿元抢劫案”,因为警方放出了一些嫌疑人的信息给媒体,不但没有抓住真凶,反而让许多怀疑对象的人生彻底破灭。新闻记者对于新闻线索的嗅觉与警方的谨慎形成一种张力,也将这种矛盾带给了读者,孰是孰非确实耐人寻味。
“自己的过错”和每个人的责任
《火车》是宫部美雪另一部较知名的作品,其原型也有真实案例。日本女子福田和子因为*人畏罪潜逃15年,一路走过大半个日本,并且不断地整容,这种极富传奇性质的犯罪经历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关注。《火车》中的主人公、银行职员和也正兴高采烈地采购结婚用品,要和女友彰子结婚,当他发现女友并没有信用卡的时候,便为她申领,却被告知这个名字上了信用黑名单。和也找到彰子询问,彰子却比他更吃惊。第二天,彰子失踪了。和也托人调查,发现她的一切竟都是假的。这充分展现了日本“陌生人社会”的现状,个体进入社会试炼场的那一刻起,一切的遭际都附有强烈的随机性,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个人社会,以至于个体陷入困境之后的*乃至呼救都会显得微不足道、无人关心。

《火车》,[日]宫部美雪著,张秋明译,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16年1月版。
宫部美雪的小说里常会出现这样的表述——“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或许结果会不一样吧。”——舞台上的个体常陷入这种进退失据的彷徨窘境。比如《模仿犯》原著中的塚田真一,原来的家庭生活幸福祥和,无意间向同学透露了自己家将接受一笔遗产,导致全家被*,虽然事后所有和真一有关系的人都向他一再表示不必自责,但是真一心中的心魔已然在目睹灭门惨案之际生成,他始终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而担心失踪外孙女的有马义男则展现了日本“团块世代”的坚韧和毅力,这位老人被罪犯连番戏弄,参与了一场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游戏”,最终迎接他的是亲人的死亡,在与看不见的凶手对垒时,他始终没有放弃。

台版《模仿犯》主人公检察官郭晓其(吴慷仁饰演)
台版《模仿犯》中,塚田真一的设定被嫁接到了主人公检察官郭晓其身上,还认真地为他添了一场前戏,郭晓其身为检察官对出人头地不感兴趣,反倒对日常繁琐的民事案件颇为用心,当他看到疑似*害养父母的少年时,立刻想起了自己亲眼目睹全家被*的往事,他重新调查被忽视的现场证据,并且为无辜者伸张了正义。由于编剧这一巧妙结合,叙事主角之后对于案件的追寻有了强大的动力,更为后续剧情的展开埋下了伏笔。如果说原著展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所谓“牵绊”有着日本文化的疏离感,那么这一版的改编更能调动中国观众的情绪和思索,也更为恰切地展现了我们所在的文化圈内个人责任的意涵。

《个人的体验》,[日]大江健三郎著,王中忱译,猫头鹰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
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个人的体验》中主人公的孩子天生残疾,他非但没有回护家庭,反倒选择了逃避,搞起了婚外情。这或许是大江一辈的日本作家都有的迷思,陷入困顿第一反应都是逃避乃至放纵。初初接触日本现代文学,肯定会为其中的伦理不明、道德败坏感到吃惊,纵观明治维新为起点至今的日本近现代史,他们曾经一度高扬的乐观主义已荡然无存,改造社会的理想向内不断地塌缩为个人的园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推理小说的“社会派”应运而生,承担起了某种对于社会的责任。宫部美雪以及东野圭吾们与前辈松本清张等最大的区别就是,推理故事不再是一个“箱庭式结构”,它们的背景就是现在的日本社会,他们也不太会再设计巧夺天工的*人动机,往往十分普通的日常原因就足以产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