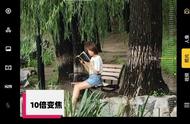故乡的选择
"你别走,我有话和你说。"
冬日的村口,孙小琴拦住了我的去路,羽绒服在寒风中显得单薄。她的眼睛里有我读不懂的坚决,脸颊被冻得通红。
我叫张志明,九九年,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回乡任教。这天,是我去县城相亲的日子,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
"志明,你真要去相亲啊?"小琴的声音有些颤抖。她比我小一岁,从小我们就在一个生产队,一起放过牛,一起上过学,如今她在镇上供销社上班。
"家里安排的,推不掉。"我低着头,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指,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远处,父亲骑着他那辆用了十多年的二八大杠等在村口拐弯处,那车子是他当年结婚时买的,如今车把都磨得发亮。
"你爹还真急啊。"小琴顺着我的目光看去,轻声说道。
回乡这半年,家里人操心我的婚事,比我自己还着急。三十岁的男人,在九十年代末的农村已经算是大龄剩男。母亲逢人便叹气:"人家城里姑娘谁嫁到咱农村来?我儿子大学毕业又怎样?还不是得回来教书?"
村里像我这样考上大学又回来的没几个,大部分都留在了城里。我回来,一是因为父亲的病,二是因为分配政策。那时候,分配已经不像七八十年代那么铁板钉钉,但也不像现在这样完全自由。
"听说对象是县财政局的?"小琴咬了咬嘴唇问道。她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是那种乡镇上流行的款式,看起来朴素又体面。
"嗯,王主任介绍的,说人家姑娘叫刘月华,在县财政局上班,铁饭碗。"我不自在地回答,脚尖踢着路边的小石子。
北风吹过光秃秃的杨树,发出呜呜的声响。那些树是我们上小学时栽的,如今已经长得比房子还高。

"那挺好的。"小琴半晌才说,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吹散。
远处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正在播放着《新闻联播》的片段,断断续续的声音飘在冬日的空气中。村口的大队部前,几个老人正坐在晒谷场的水泥地上闲聊,烟袋锅里的烟丝燃着火星。
这次相亲是全村人都知道的大事。我爹张大河为此特意从镇上供销社买了一套"的确良"衬衫,还有一条"西化"的裤子。那裤子在当时已经是很新潮的了,不再是那种老式的中山装。
"儿子,咱家条件不好,但你是正经大学生,硬件不行,软件得跟上!"父亲穿着他那件褪了色的蓝色中山装,严肃地对我说。他那双常年干农活的手,骨节粗大,皮肤粗糙,拍在我肩上有种沉甸甸的分量。
临行前,母亲絮絮叨叨嘱咐着:"人家姑娘家境好,你可别挑三拣四。咱们农村人,能攀上县城干部家庭,那是祖坟冒青烟了。你看隔壁李大爷家的儿子,不也是找了个县医院的护士,如今孩子都上小学了。"
母亲说这话时,一边往我衣服上摘着看不见的线头,一边偷偷擦眼泪。她的手上全是老茧,那是几十年操劳的证明。
但此刻,站在村口的小琴,却让我心里泛起涟漪。她站在那里,像是与这个萧条的冬日格格不入的一抹亮色。
"我有东西给你。"小琴从她那个带着补丁的帆布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这是省城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简章,还有...这是北京那边发来的函授资料。"
我愣住了,接过信封。封面上印着"九九年招生简章"的字样,已经有些皱了,但被人小心翼翼地保存着。

"你怎么会有这些?"
"你不是总说想继续读书吗?"小琴的声音变得有些激动,"我托在县邮局工作的表姐帮你留意的。你在学校教书,平时不方便出去打听这些事。"
风吹乱了她的刘海,露出光洁的额头。我突然想起高中时,她总是坐在我前排,每次发卷子都会回头给我一个鼓励的微笑。那时学校条件艰苦,一个教室塞四五十个学生,夏天热得汗流浃背,冬天冷得手指发僵。
"我还记得你说过,想去更大的地方看看。"小琴继续说道,眼睛亮亮的,像是冬日里难得的一抹阳光。
我握着信封,感到一阵温暖从指尖传来。那年代,这样的资料可不好找,小琴一定费了不少心思。
"爸的病..."我欲言又止,父亲去年查出了肺病,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在农村,缺医少药的,总是让人放心不下。
"叔叔的病已经好多了,上次我去你家送姜茶,看他气色比去年强多了。"小琴认真地说,"再说,你留在这里就能照顾好他吗?你又不是医生。志明,你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远处,父亲不耐烦地按着自行车铃,"叮铃铃"的声音在冷清的村道上显得格外突兀。
小琴似乎看穿了我的犹豫,又补充道:"你记不记得咱们初中时看的那本书?《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不也是不甘平凡吗?咱们县二中的图书室,你几乎把那本书翻烂了。"
我心中一震。那确实是照亮我青春的一本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让我第一次明白,即使是平凡如我,也可以有不平凡的梦想。
"可是,那个刘月华..."我犹豫着,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内心的纠结。

"我听大海嫂说,她爱打麻将,最烦农村人了。"小琴直视我的眼睛,语气突然变得坚定,"志明,人这一辈子,能有几次选择的机会?"
那一刻,我的心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是啊,三十岁的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父母安排的平稳生活,一边是自己心底的渴望。
"志明!磨蹭什么呢?再晚赶不上县城的汽车了!"父亲的吼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去吧,别让叔叔等久了。"小琴向后退了一步,仿佛是在为我让路。
去县城的路上,坐在拖拉机改装的"农用车"上,父亲滔滔不绝地讲着刘家如何如何条件好,什么财政局的工作多么稳定,退休金多么可观,而我却一直想着小琴递给我信封时的眼神。
农用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车厢里挤满了赶集的农民,有人带着鸡,有人背着筐,车上弥漫着汗味和烟味。这是九十年代末农村通往县城的主要交通工具,每趟车五毛钱,比自行车快多了。
县城比村里热闹许多,街上的"大金鹿"彩电、"长虹"彩电的广告牌随处可见,有些商店已经开始卖VCD了。街边小摊上放着张学友、刘德华的磁带,音乐声嘈杂地混在一起。
相亲地点定在县城最好的"红星饭店",听说一盘红烧肉要十多块钱,够村里人吃一周的了。
刘月华确实漂亮,穿着时髦的喇叭裤和高领毛衣,发型也是最新流行的"波浪卷"。她的指甲涂着鲜红的指甲油,这在我们村子里是从未见过的新潮。
她的父亲是财政局的中层干部,一脸的官相,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话时总是带着一副居高临下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