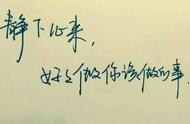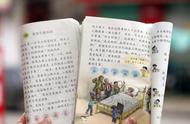太阳每天很准时的散发着热,这几天,云朵似乎失去了踪迹,一到午后,气温就升的很高,热的让人想睡个觉,及时做个凉快梦。沸腾的白天一过,人们感觉浓度不够,于是,带着有度数的酒,外加几个小串,对着夜色,小酌几杯,大声说几句,颠三倒四的话,才算是完整的一天,北方的夏日,直接干脆,昼与夜,一热一凉一杯酒。
连着几天的黄昏,都会准时来一场雨,很急,直上直下,从空中倾倒着下来,风却很小,几分钟,地面就降了温,清凉的感觉透着植物的味道,开始弥漫,这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雨后,空中会出现一轮月,或圆或钩,幽暗轻柔,煞是可爱 。

人们都喜欢月光,不分南北,不分国界,男男女女也都愿意在月下散步,谈情,说悄悄话。邓丽君当年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定情的见证,也定格了青春的岁月。
中学时期,家里住房小,每日做功课只能在狭小的厨房支个书桌,好在有个凉台,夜深时,愿意站在窗口,望外面的夜景,那时的月很清澈,高高挂在那儿,把距离和空间,陡然的变大了,让我做功课的小地方,变的宽敞起来,累了,抄几首关于月夜的古诗,美句,成为少年时,独特而美好的记忆。城市的月总是时隐时现,高楼林立的上方,总有些云在晚上出来,遮挡一番,心急的人,总会错过,所以,有时只能对着一幅忽明忽暗,朦朦胧胧的图,却不能对话。最喜欢的月光,在乡下,在姥姥家,小时候,一到暑假就迫不及待的赶过去,热热闹闹的玩一个假期,自由自在,没人管,一到晚上,青蛙鸣叫, 蟋蟀“嗡嗡”的忽闪着翅膀,院落的狗也偶尔叫几声,各种声音,忽远忽近,这时候的月亮,安静的,倾泻幽幽的光,明亮透彻圆盘,像刚洗过的一样,闪耀浮动,青而淡,不言不语的用含蓄光泽和大自然对着话。

后来有一段日子,几乎把它忘了,早出晚归的忙,床变成我依恋的地方,往头顶上看,只有天花板,没有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蓝颜”这个新名词,记得,一段文字配着插图,那上面,月是蓝的,一对男女在画面,并肩坐着,若明若暗,恍彷迷离,传递着一种陌生的情感,很唯美,被誉为游离于亲情、爱情、友情之外的“第四类感情,用月来做装饰,也许恰如其分,男女知己可以说心里话,取暖方式是心灵,也恰好是冷*,如果炽热了,用身体取暖,就成了红颜,要么失去,要么会升级为故事。月在空中,偏冷,凝聚,收敛,那种阴柔之美总隔着距离,但稳定,持久,给人永恒的感觉,红颜,蓝颜,爱情,友情,都愿意把这种柔美的感受,寄托在月的无限而漫长的时空里。
关于月光的美,大自然美,发现者大多是文人墨客,间或是陷于感情旋涡的痴男怨女,寄予情感在这份柔暗的光辉,月儿成了知音,有了人性,变成有生命,有情意的天使,普照与心,彼此感应。那些写成诗的,赋成词的,回荡在歌声里的,被人们拉扯着,走进了梦。月是圆的,月是纸的,月是油的,月是相思的……但对于每日奔波生活的人,往往不会注意它,也许一盏灯来的更实惠一些,每个人的世界不同,美的视角也不同,当情绪盈满,圆缺时,它总是变幻出不同的解读,时而活跃,时而宁静,步履轻盈的走来,淡雅素洁,脉脉含情。
北方的人们,不钟情于月的臆想,更愿意把它变成实实在在的美食,中秋的月饼,小吃店的麻团,元宵节的汤圆,节日一到,对月勾起思念时,就会端到眼前,煮的,煎的,炸的,捏成团,揉成饼,甜咸酥脆的装扮起来,拉近与月的距离,感受它实实在在美,放在肚里,化成回味。其实任何季节,凡是十五的月亮,只要不被乌云掩遮,都会同样的大放光明,南北互汇交触,魅力常驻,永不衰败。

还是喜欢图片里蓝色的月亮,也许有知己在上面,有秘密可以倾诉“待月西厢,拂墙花影”,四季总有礼物,不断的呈现,昙花一现,燕飞莺鸣,飞鹤冲天,冬来,春又来,在无限的时空做有限的表演。但只有月代表了无限,代表永恒的柔美。此时的月在北方,柔柔的,泛着蓝色的柔情,“清风拂山岗,明月照大江”,月是故乡的月,江是松花江。
一杯酒,一顿烧烤,解决了白天的的酷热,一轮月,会带你入梦,去咀嚼杂陈的人生滋味,憧憬,思索,美好的未来,此时,高挂的月,正宁静的徘徊,蓝月色,蓝颜,与月上下,遥相 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