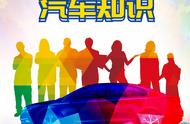1932年,陕西农户王家的幺女出生,取名王芝霞。
这孩子常啼哭不止,父母兄姐轮流哄都没用。母亲爱女心切,抱起孩子往外走,说要到香积寺请法师驱魔。
此言一出,孩子的哭声竟收住了。刚进寺院,她忽地睁开一双大眼睛,滴溜溜追视着大殿和佛像,咯咯笑了起来。
自此,只要王芝霞一哭,家人就把她带到庙里去,准变“乖乖女”。稍大一些,她不跟孩子们玩耍,反而常常独自去逛寺庙,还会翻阅经书,哪怕看不懂也一脸向往。
村里人议论说,这闺女与佛有缘。谁承想,多年后这话成了真。

18岁时,王芝霞与邻村一名青年结婚生子,温馨喜悦让她逐渐遗忘了圣洁的佛堂。
25年后的一天,王芝霞偶然走进香积寺。肃穆的钟声,庄严的佛殿,明亮的烛火,一瞬间唤醒了她脑海中关于佛的记忆。
那之后,王芝霞总是梦见佛祖用慈悲的目光注视着自己,像是声声召唤。时间一长,“出家”的念头便油然而生。
孩子已经大了,父母有兄姐照顾,没啥可操心的了,她要去过另一种人生。
可是,王芝霞的心意却遭到了全家的一致反对。

在那段不被理解的时光里,王芝霞也在求佛与凡尘二者间,纠结不已。
一番思量后,她还是作出了取舍。
任凭家人苦劝哭求,她仍义无反顾地到香积寺削发为尼,从此红尘已逝,古佛青灯。
王芝霞很快习惯了晨起诵经、茹素打坐的枯寂生活,但对亲人的思念让她倍感煎熬。
丈夫和儿子曾数次到寺中劝王芝霞还俗,她亦萌生退意。然而,她并没有脱下海青,回归家庭。修佛的执念令她羞愧难当,觉得自己六根不净。为了彻底戒除杂念,她离开香积寺,走进了终南山。
那年,47岁的王芝霞用黄泥、枯草、木头和石块搭建起一间小庙,取名“三圣殿”。逼仄的屋子靠煤油灯和蜡烛照明,一头塑佛像、摆供桌,另一头则用来坐禅休憩。

她在屋外开了菜地,加上些野菜野果和山民送的供养,日常吃食倒也足够。
除了修行做活,王芝霞还潜心钻研中医,常采回草药晾晒炮制。她会定期背些药材下山换米油面,其余的便留着自用,或免费为村民医治。为此,村人们对她格外敬重。
王芝霞常在门口放上茶水,无偿供爬山的游人饮用。人们感谢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口耳相传间,香客多了,媒体也慕名造访。
这时,却有人揣度王芝霞佯装修行,沽名钓誉才是真的。
可不论虔诚的香客或猎奇的媒体,王芝霞从未索取分文。她的生活是清苦的,数十年来自给自足,凡事亲力亲为。
尽管如此,她抛家弃子的行为还是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