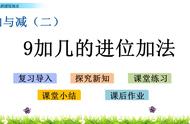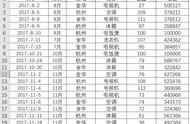陈延年出现在电视剧的开头和结尾
经济观察报:这里面还有一些虚构的情节和虚构的人物,对虚构的情节是怎么考量的?比如,*和陈延年在路灯下相遇相识,这好像是没听说过的。
龙平平:你首先要有一个概念,这是个电视剧、是个文艺作品,他要反映历史,但又不是复制历史,那我要有一个合理的架构,*在北京的时候,究竟见没见过陈延年,没有记载。甚至说陈延年那时在不在北京也没有记载。
那这个时候,需要一些合理的虚构,因为五四运动前后,*确实在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后来我们努力查到了,陈延年也确实在北京。*后来曾经提到过陈延年,对陈延年评价很高、很佩服。那么,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虚构,但也不能编的太多、不能过分,只是适当的虚构,设计一个他们相遇、相勾连起来的情节。
虚构的人物,在《觉醒年代》里有三个,分别是柳眉、郭心刚和张丰载。其中张丰载是唯一的坏人,这个人也是有历史原型的,叫张厚载,这个人其实不是个坏人,而是研究戏剧很有成就的人,但在历史上,张厚载确确实实在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中,因为挑拨离间,被北大开除了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虚构出了一个反面人物,其实你也能感觉到他是虚构的:一个学生居然一跃而成为京师警察厅的密探。
还有一个人是郭心刚,郭心刚是有原型的,由两个人合成,一半儿是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烈士郭钦光,郭钦光当时患有肺病,在游行示威中劳累过度、呕血而死,当时全国各地为他开追悼会;另一半儿是谢绍敏,就是在游行中撕下衣襟、咬破手指,写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的。通过两个人的集合,同时把郭心刚设计为青岛人,这样就把故事串了起来。
经济观察报:就本剧展现的6年历史来说,青年*和*,客观上说不是重要人物,本剧为什么也给予了不少篇幅来展现?
龙平平:我们就那段历史而言,除了南陈北李,青年人中如果论参与程度的话,张国焘、赵世炎、邓中夏,都是较为靠近中心的人,*和*就要排在后面了,但他们作为参与者,也有呈现的必要。
其中,邓中夏、赵世炎和李大钊以及陈独秀的接触是最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里就有赵世炎,1920年5月时,赵世炎去了法国,而且是带着使命去的,显然在建党过程中,赵世炎是比*更靠近中心的人。
张国焘也是很难回避的人,他在建党时做了很多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是张国焘主持的,而一大选出的职务,张国焘仅次于陈独秀,他的党内职务甚至比李大钊都要高。
但客观来说,*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接触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受到了影响。所以,给*的笔墨多一些,也是为了呈现青年*的进步,我们站在党史全局来看,在井冈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那么他是怎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也应该展现。
所以,我们虽然呈现的是这6年的历史,但对于具体人物,还要考虑他的全局、考虑对他的定论。比如陈独秀,他在这段时间是光芒四射的,如果你回避陈独秀,就是片面的,这段历史就讲不清楚;但如果你完全把他扭转过来,也是不合适的,他毕竟在后面犯了错误,对他的展现,也要考虑后面的因素。所以你也注意到了,对他性格上的缺点,也进行了细致刻画,这就是为了统筹这个人物,进行的合理的设计。
经济观察报:我有些理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难”了,对这些人物的设计、在剧中的篇幅,既要尊重历史事实,也要服从于这个人物在党史中的整体评价?
龙平平:是的,就是对于*和*,尽管在这段历史的大事件中相对边缘一些,但他们后来的贡献很大,那我们就需要把建党前他们的成长历程反映出来。
《觉醒年代》里也有*的戏份,其实*那时候年纪很小,还是个中学生,他也不在北京,参与感就更弱了。但是就整个党史来统筹考量,*在后面非常重要,那在这个阶段也需要展现,而剧中的有关觉悟社和旅欧党小组的一些情节,也是历史事实。

青年*的思想成长在电视剧里得到了充分展现
经济观察报:我看您在接受采访时,屡次表达了对陈延年这个人物的喜爱。
龙平平:说实话,在《觉醒年代》这个剧里,虽然陈独秀是主要人物,但我最想写的还真不是陈独秀,而是陈延年。前一段时间也不小心说漏嘴了,我的下一部作品,就是写陈延年、赵世炎和*三人。
这也要从《我们的法兰西岁月》那部电视剧说起,原来的剧本里没有陈延年,因为当时思想还不解放、不敢写。一位前国家*曾经把我们叫到家里面,谈了一个下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材料。
这位*提到了陈延年,说如果谈赴法勤工俭学这段历史,陈延年是不可或缺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提示。回来后,我和编剧李克威商量,把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补了进去。后来,老领导陆续给了我不少材料,我开始研究陈延年、赵世炎。为了研究陈延年,我循着他的人生轨迹走了一遍,凡是陈延年工作生活过的旧址故居,上海的、北京的、法国的、广州的,我每个地方都去了。
可以说,研究陈延年对我的影响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陈延年在选择理想和信念时,是最典型的、最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经历也比同时代的人丰富得多。你看他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时,他是很痴迷的、很坚决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他后来又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是不容易的,他比别人多一道坎儿,所以他的转变,在当时的党内引起非常大的反响。
陈延年这个转变过程,反映了这个青年在寻求最完美的理想社会,他为什么信仰无政府主义,就是因为当时的无政府主义,从形式上看是最美好的社会形态: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家庭,当然也没有阶级、人人向善友爱,互帮互助,那听起来,这就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啊。
所以陈延年太不简单了,他追求的是一个理想社会,还去亲身实践,他与父亲陈独秀的不同是,他认为要拯救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就不能像陈独秀那样又要家又要国,结果只能给家庭带来不幸。所以他17岁就为自己定了六不: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谈恋爱。他能提出这六不,说明他是有条件照相和下馆子的。
在那个时代,陈延年曾是个公认的天才,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决心不谈恋爱、不结婚,完全献身给社会,29岁牺牲时还是单身。你还能找到比这更经典的理想主义吗?
经济观察报:所以您就特意为陈延年设计了一段儿感情戏?
龙平平:对,这就是柳眉的由来,是我给他安排的伙伴、无政府主义的同志,这里你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说柳眉是陈延年的女朋友。他们其实是同志关系,柳眉因冲突而遇见陈延年,从看不起他、到被他折服、然后追随他,来展现他们追求美好社会的过程,所以有了实践互助论的实验,结局必然是撞得头破血流啊,通过柳眉这个虚构的人物形象,来反映陈延年探索真理的过程,反映陈延年的品质、反映他的执著,增添戏剧化情节,这样故事就生动的多,人物也会更加鲜活。
那么柳眉的结局是什么?在电视剧里没有交代,在即将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觉醒年代》这本书里,对这部分就说的更详细了。我认为这就属于小事不拘,是合理的虚构。而根据查到的材料,当年确实是有人追求过陈延年的。
这里我想告诉年轻观众的,就是说100年前的那个时代,确实有这样一批青年人,他们以这样的觉悟来投身社会。
经济观察报:陈延年就是您心目中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的杰出代表?
龙平平: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这个感觉是对的了,如果说《觉醒年代》在青年人中引起了反响,恐怕陈延年这个人物就是第一位的。播出后,我到好几个大学里做交流,有同学跟我说,现在我们中间谁要说不知道陈延年,会让人笑话的。
我前几天刚从合肥延乔路回来,那里还是鲜花满地。那些少先队员给我感动的呀,围着我让我签名,签到衣服上、签到红领巾上,他们不是对我龙平平感兴趣,他们是对烈士的崇拜啊。所以呢,我这么执拗地非要给陈延年加戏,也算得到了回报。
经济观察报:从党史上看,陈延年应该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
龙平平:历史上,最早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小组的是赵世炎,其次是*、再次是陈延年。后来,陈延年和赵世炎到了苏联后,*便担任了共青团旅欧支部的*。后来,这三个人又先后回国,成为中共早期重要的*,赵世炎和*去领导上海的三次武装起义,陈延年去领导省港大罢工,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友情也很深厚。
陈延年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曾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列宁,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领袖。1927年召开党的五大时,大家都认为陈独秀不行了,要另选新的接班人,有材料说,共产国际曾经想让陈延年出任党的*,但陈延年不干,他说他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去江苏担任省委*,那时去江苏就是去上海,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结果到了不久就被抓了、很快就牺牲了,太可惜了。
然后,赵世炎接任陈延年,结果没过多久,也同样被捕牺牲。两个最好的战友先后罹难,*当时是伤心欲绝啊。陈延年牺牲不久,中央特科不惜代价,很快将出卖他的叛徒打死了。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专门发表社论,称陈延年赵世炎之死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生命上一个永不磨灭的黯然的伤痕。解放后,*还专门找到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请她写回忆陈延年的文章。
应该说,陈延年、赵世炎和*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都有着杰出的才干,三个人也有着深厚的友情,可是前两位都献身了革命,只有*走到了最后,成为新中国的总理,你可见革命的残酷性。
学习*的思想解放
经济观察报:您长期在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党史研究是您的专长,尤其是对*的研究,公众好像不太了解这个研究机构的设置,您给介绍一下吧?
龙平平:我是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就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一直干到2016年退休,然后返聘接着干,直到现在还是返聘着。这一辈子就研究党史,中央文献研究室原来就是研究领袖的,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合并后,叫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我是研究*的,当了很多年的*研究组的组长,所以说,你说我是专家、尤其是研究*的专家,这个我一点儿也不推辞,起码对*的研究,恐怕很少有人能像我一样,接触到那么多的一手资料。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最早的名称叫做*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就是编辑毛选(《*选集》)的,这个级别当然是很高了,成员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是毛选编辑委员会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最早是汪东兴负责,后来是胡乔木负责。之后改名为中央文献研究室,我们的研究范围也相应扩展了,扩展了也并不多,只研究10位领袖同志,我一直在三部,三部就只研究*和陈云。
我们研究领袖人物,主要就是三件事,我们叫“老三样儿”,就三部(也称*研究组)来说,先是《*文选》、再是《*年谱》,最后是《*传》,我之所以还返聘着,就是因为《*传》下卷还没出版。
经济观察报:那您是怎么从党史专家介入到影视剧创作中来的?
龙平平:这还是从“老三样儿”演变过来,你有了书,自然后来就有了画册,再后来就是纪录片,纪录片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之后就开始了影视剧创作。这个事情呢,别人干不了,他没有那么多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没人能准确把握。
所以,我们最早参与到影像的创作中,应该是纪录片《*》,那是1997年——也就是在小平同志逝世那年播出的,不知道你有印象没?那时你多大?
经济观察报:那时我上高中,但我对这部纪录片有印象的,后来也多次重播。
龙平平:在纪录片之后,接着是电影《*》,这部电影2003年上映,坦率说之前很多人在搞,但屡次都通不过,才把这个任务给到我这儿的,由我和另外一位同事来当编剧,由丁荫楠导演、卢奇主演。因为题材重大,几乎拿了所有的奖项,卢奇还拿了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那么在电影《*》之后,就该出电视剧了,这就是《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其实这个电视剧策划时,先有了一部电影,叫《我的法兰西岁月》,展现的就是*赴法勤工俭学的故事。这个剧播出后,反响也很大,有很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都热议这部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当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很多,而当时*的年纪很小,更多的是一个追随者,这就显得对那段历史呈现得不完整。
当时,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希望补充一下,把这段历史完整呈现出来。所以,后来的电视剧,“法兰西岁月”前面的定语从“我的”变成了“我们的”,那这个“我们”到底是谁呢?那可实在太多了,*、蔡和森、赵世炎、陈毅、聂荣臻、李立三、李维汉、王若飞……我们专门开了一个会,邀请这些赴法勤工俭学的革命家的子女、后代来研讨,共来了100多人。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这部电视剧,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出品单位之一,我是作为三部主任参加创作的,可以说是项目负责人。第一次参加电视剧,又是职务关系,所以用笔名署了个剧本顾问,主要是表示个责任吧。那次是我第一次参与电视剧的创作,这部剧也有不少曲折,让我体会到了这里的不容易,也让我接触到康洪雷这样优秀的导演,受益匪浅。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剧照:画面里依次是*、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李富春
经济观察报:这两部电视剧有个共同点,都是集中展现了建党初期那些进步青年的生活和追求,这些是否都有充足的史料可供参考?
龙平平:《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这部电视剧,就是呈现青年们的风貌的。我去过法国很多次,有一次我专门去拜访了法国一位卸任的*,我见到他时,还没提问呢,他先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当年中国在全世界的留学生很多,为什么在法国的出了那么多人才?
这也是事实,共产党的杰出*,有很多都出自法国留学生。我在电视剧里,还曾刻意加了一段旁白:那个小屋子里,后来出了新中国的一半儿的总理和副总理,*、*、聂荣臻、陈毅、李富春。等等。
经济观察报:那位法国*的问题,您是怎么回答的?
龙平平:我其实并没有正面回答。他提这个问题,当然是抒发一种自豪的情绪,意思是法国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所以才孕育了中国这批杰出的*。但这个提问也触发了我的思考,因为陈独秀最早就是法国派,他的思想深受法国人的影响。
那么*的思想启蒙,毫无疑问就是在法国,因为他15岁就到了法国,那时还是一个青少年,就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可以说好的坏的都深刻领略到了。一方面,他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是中国需要学习的;另一方面,他也亲身体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不可克服的矛盾。
试想一下,*如果在法国上了学,或许不会有这个选择。正是因为他是个勤工俭学生,是在法国的社会最底层打工,接触了底层的劳动人民,见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有了深刻体会,才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经济观察报:那段时间正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
龙平平:是的,我的下一部电影,就是想展现青年人的长成,讲述一个普通青年如何成为特殊材料的,着重就是想围绕陈延年、赵世炎和*在法国留学和回国后领导中国革命最后两人英勇牺牲的这段历史。
经济观察报:这段历史或许有一个看点,就是这些*那时正值青春,有很多和青年人的共鸣之处吧。我想到一个情节,《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展现了一些*和张若名的感情戏,这也是历史事实吗?
龙平平:当然是历史事实,*和张若名一同在觉悟社、又一同留法,确实有过一段交往。但两人的志向并不一样,*是要做职业革命家,他去法国不是去上学的,而张若名考上了大学。后来,*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同是觉悟社的战友邓颖超,张若名和同样留法上了大学的杨堃结婚了。
说起这个还有些奇妙的缘分,我就是杨堃的学生,我是北师大历史系78级的,杨堃教我们民族学,我本科毕业时本来想考杨堃的研究生,而杨堃建议我考吴文藻的研究生,就这样我又成为了吴文藻的关门弟子。*的这个故事,就是杨堃先生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
对于赴法勤工俭学这批青年,陈独秀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勤工俭学生去了好几千人,很多人都上不了学,其中蔡和森和陈毅都被遣返回来了,*中只有聂荣臻等少数人上了学,赵世炎和*都没学可上。那么这种情况下,陈独秀1923年去了莫斯科,他就对斯大林说,你如论如何要把留在法国的这批中国留学生接收过来,这才促成了莫斯科东方大学接纳这批法国留学生,后来陆陆续续,赵世炎、陈延年和陈乔年都去了莫斯科,再后来是*。
所以,赴法勤工俭学的这批青年,一批被遣送回国、一批转道莫斯科,一批留在法国上了学,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而在法国上了学的这部分人,后来不少也都成为了大师,例如杨堃就是开创中国民族学的大师、张若名也很了不起,还有画家徐悲鸿、潘玉良,也是当年的法国留学生。
用平和的立场讲述党史
经济观察报:在您参与创作的几部电视剧里,对一些在党史中有争议、甚至是最终走向反面的青年人,也给予了客观呈现,这些人物在创作中该如何把握?
龙平平:这些人,在剧本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后来成为国民党,比如傅斯年、罗家伦,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是先锋人物,是学生领袖;在五四运动中,谁能比傅斯年和罗家伦的作用大呢,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会主席,他就是游行总指挥;罗家伦,他是起草宣言的人。这些人呢,我们要再现这段历史,就需要展现他们,不违背历史事实,但是也不刻意渲染他们。
还有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后来有叛党和脱党的。像张国焘、陈公博,这是两个叛党的;罗章龙,后来犯了错误;张申府、刘仁静是脱党的。张国焘、张申府和刘仁静其实是最早的党员,曾是党的*,这些人物,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都给予了客观呈现。
好比张国焘,我们当然不可能像展现*那样去展现张国焘,但如果你抹掉这个人物,那你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就好比那时的汪精卫,我们也不能把他当做反面人物来写,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进步青年,叛党叛国那是后来的事,但这不是说我们不考虑,他们后来的事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那么,在篇幅上、在表现的形式上,都要和其他人物有所区别。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有正确的历史观。

《历史转折中的*》电视剧里华国锋的形象
经济观察报:在《历史转折中的*》这部电视剧中,突破也不小,对华国锋和胡耀邦的形象的塑造,也让人非常深刻。
龙平平:华国锋和胡耀邦的形象,在那个剧里也是一大突破。因为他们在那个历史时期做出了贡献,很多人都说,你要反映“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你不讲华国锋还叫什么历史。
在那部剧中,有名有姓的党和国家*至少50个以上,而且好多都还健在。作为电视剧,必须要有艺术加工,没有艺术加工就成历史书了,但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又必须以真实为基础,这是写那个剧本最难处理的。
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首先是尊重历史、敬畏历史,也就是常说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个说着容易,做起来其实是需要勇气的。这么多年,我研究*得了一个真传,就是解放思想,我一直认为没有什么题材是不能写的,党中央没有设禁区,关键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观点、用什么方法来写。
比如,对华国锋同志,既要对他的历史贡献给予充分反映,也要对这一阶段他的局限做必要的交代。
经济观察报:我还注意到,在展现1976年那段历史时,当时的一些*,例如副总理吴桂贤也出现了,我看的时候也很吃惊,好像在之前的影视剧作品中,很少能看到她的形象。
龙平平:这也是历史事实嘛。粉碎四人帮那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吴桂贤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她是在场的啊。不止是吴桂贤,还有陈永贵、倪志福、苏振华,这几位*都在场,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有谁就有谁,是谁就是谁,吴桂贤不仅在场,还有台词,不过台词是我设计的。
经济观察报:在《历史转折中的*》里,也有两位重要的虚构人物,这两位是很多真实人物的集合体吗?虚构他们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龙平平:我不客气地说,我在这方面是比较大胆的。以前,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中,对虚构人物的设计,是有严格限制的。但在《历史转折中的*》,就突破了这个限制,而且突破的尺度很大。
最大的突破就是虚构了这两家人,田志远一家和夏默一家,而且级别都是正部级干部。过去,虚构人物有个明确的规定,虚构的级别不能到副部级,因为到了这个级别,就会有人对号入座,观众就会猜这是谁、那是谁。但这个限制,在拍*时必须突破,因为你的角色要经常见到*,能见到*的人,级别怎么可能低?如果没有这个虚构,就构不成故事。
经济观察报:其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何进行守正创新,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了,既要尊重历史,又要让历史融入当代传播语境,焕发感召力,具体到我们谈到的这几部电视剧,您秉持了什么样的历史观?
龙平平:就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来说,我觉得我用了一种平和的、客观公正的历史观来看问题,用百年大党的成熟思维来回望百年前的历史、来展现这些历史人物。
这个你从《历史转折中的*》中也同样能感受到,例如刘鑫、曹慧、曲径,他们或许站在“两个凡是”的立场上,在剧中呈现的是思想有些守旧的人,但是我不希望观众对他们有恶感,希望能理解他们的言辞和做法,这样会触发你的思考:他们为什么会那么说?会那么做?
这种创作思路,在《觉醒年代》体现得更加充分,例如北洋政府这批官员,包括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甚至包括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我都避免把他们贴上坏人的标签,首先我们没有厌恶他们,而是把他们作为那个时代的正常人物来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