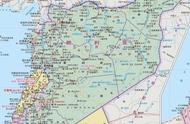《妈妈!》电影剧照。
新京报:如果不能及时从母职退休,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于玲娜:这个问题的原因也是文化性的:退出母职以后去哪儿呢?很多妈妈没有地方可去。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位中老年女性,你觉得这个社会上有哪些事情是鼓励你去做的呢?又有哪些场合是欢迎你去的呢?
以前我见到中老年女性最多的场合就是广场舞和菜市场,现在是好多了,还能看见她们去旅游,扬着丝巾拍照。但她们应该去开会(参与)啊,应该更多出现在新闻画面里,那样也许她们就会很乐意退出母职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大多数的女儿要么变得和母亲一样,要么成为和母亲截然相反的人,为什么很多人提到母女关系的时候,更多的会感觉是一种“相爱相*”,总是伴随着爱和伤害,不像其他亲子关系那样,至少在直觉上是温暖、亲密的呢?
于玲娜:关系里的相爱相*,常常是因为又近又像,空间上靠得太近,又有很多相似的部分,就容易相爱相*。但相爱相*不一定是坏事,它作为一种鲜活的关系形态,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嗑CP(网络用语,主要用来形容情侣),有些人喜欢嗑温暖亲密的,有些人却觉得相爱相*的嗑起来更香。
新京报:这种“相爱相*”的关系本质是什么?如何避免呢?
于玲娜:我觉得相爱相*,意味着两个人可以互为镜像。她们都有可能从这段关系里得到很多成长,所以不用刻意避免,只需要多反思多觉察,在关系中积极成长。
新京报:能分享一些普通家庭可以采用的疗愈的方式吗?
于玲娜:我很难在这里开药方。心理学的复杂之处,就在于人和人实在太不一样了。要解决问题,我会建议大家先看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我这本书(《挣脱母爱的束缚》)花了很大篇幅讲分类,讲各种不同形态,就是因为不同类型的问题应对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另外,有问题的家庭里面,每个人的反思和成长节奏是很不一样的。最痛苦的人会最先寻求解决,而那些把症状转移到其他家庭成员身上,或者从其他家庭成员的症状中获益的人,常常觉得自己没问题,也不需要改变。
真正整个家庭都愿意一起成长的情况非常少。
所以我首先想建议大家,思考疗愈这件事不要急于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单位,个人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家庭就会随之改变。
新京报:在各种不健康母女关系中,有哪种问题更容易被我们所忽视,但其影响可能是更加深远和令人担心的?
于玲娜:我觉得,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是忽视的问题。
忽视的问题存在于广阔的时空中,整个历史叙事就是对女性的极大忽视,是为“history(历史)”。在家庭层面,中国女性遭受的最普遍的创伤就是忽视的创伤。忽视女孩的身体需求:不给她吃饱穿暖,生病了不重视,很多女孩青春期来例假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胸部发育时没有合身的内衣可穿。忽视她们的情绪需求:要抱的时候不给抱,哭的时候让她憋回去,很多女孩跟大人说话大人都爱答不理。忽视她们的发展需求:认为女孩不需要读太多书,不鼓励女孩受教育,尤其不鼓励她们探索哲学、数学、物理这些男性把持的领域。
谁在忽视呢?
父母都在忽视,但父亲和母亲的忽视性质是不一样的。父亲的忽视接近一种阶层忽视:你不如我,你不能传宗接代,所以我没必要重视你。母亲的忽视则是一种不健康的代际传承:你和我一样,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你也要这样,我不配,所以你也不配,以后你如果生了女儿,她也不配。——这样的想法是下意识的,也是非常悲哀的。

《妈妈!》电影剧照。
如果我生了一个女儿,
恐怕会比现在焦虑很多
新京报:在生活中,你也有着女儿的身份,以及母亲的身份,面对同样的问题,作为母亲的自己,和作为女儿的自己,会有一些不同吗?
于玲娜:我只有一个男孩,所以没有机会体验母女关系中的母亲位置。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生的是个女孩,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那么重男轻女了,但如果我生了一个女儿,恐怕会比现在焦虑很多。作为男孩的母亲,我只希望他轻松健康地成长,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成年后融入社会就跟我没关系了,以后都是独立的个体,没什么事不需要出现在对方的生活中。但如果有一个女儿,我觉得我需要教给她的事情太多了:怎样保护自己免遭各种伤害,怎样认清各种权力的运作方式,认清性别文化给自己带来的处境。等她长大,还得教她怎样择偶、怎样带孩子,毕竟我也得完成母职传承。我也许还会想攒一笔钱留给她,因为女人没有钱会比男人没有钱惨得多。
总之作为女儿时,我觉得我是让妈妈很省心的,因为我小时候是个很乖很自律的孩子,比同龄男孩好带多了。但做了妈妈我才意识到,养女儿是很操心的,男孩好动调皮,那种累是体力上的;女孩不一样,总感觉危险四伏,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光想想都觉得焦虑。

《母爱的羁绊》,[美]卡瑞尔.麦克布莱德 著,于玲娜 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9月版。
新京报:你过去译介了许多相关作品,比如《母爱的羁绊》《为何母爱会伤人》等,对此有一些心得感悟吗?如果从现在的视角去看这些作品,你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吗?
于玲娜:《母爱的羁绊》《为何母爱会伤人》这两本书,其实都是特定类别和理论框架下的细致讨论,比如《母爱的羁绊》,讲的只是自恋人格这一种类型的母亲。
我这本书(《挣脱母爱的束缚》)借鉴了《为何母爱会伤人》里对母职的描述。我尝试描述各种丰富的关系类型,提供一个概览的视角,所以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是和这两本书不一样的。另外,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人的心灵遇到的挑战也很不一样。
这两本书(《母爱的羁绊》和《为何母爱会伤人》)讲的都是美国文化下的母女关系,我们的文化和美国人的文化很不同。很多现象在不同文化中很难找到对应物。同时美国文化里会有更多的家庭模式,也就是小孩生活在有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的家庭里,或者父母曾经转换过自己的性别,这些情况在中国又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很多心理学理念的传播,都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即怎样去描述和处理特定文化中的心理问题和创伤。我这本书里探讨的所有例子和类型,都来自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也算是一种本土化尝试。
新京报:与其他国家相比,是否有一些和母女关系有关的问题,是在中国更为普遍的呢?
于玲娜:的确有一些母女关系问题,在中国更为普遍。
不一样的文化会造就不一样的心理问题。最典型的比如缠足,古代女孩的缠足,大都是由母亲完成的。让女儿变成“残废”,同时又是为了让女儿将来嫁得好过得好,这就成了母女关系之间一个非常复杂、特殊的事件。虽然缠足已经成了历史,但类似的事情仍然在我们文化中延续,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戏码:一边伤害你,一边说这是为你好。
简言之,我觉得我们的人心是比较“曲折”的,和其他国家的“直”有很大不同。比如中国女性常用的自虐式情感绑架:你不听我的我就死给你看!这种戏码老外就是完全理解不了的:为什么要*敌八百自损一千呢?他(她)不听你的难道不是让他(她)去死吗?

《为何母爱会伤人》, [美] 贾丝明·李·科里 著,于玲娜 邓莹 译,联合读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5月版。
新京报:为什么会想要创作《挣脱母爱的束缚》这本书?回看这本书,会有一些遗憾吗?
于玲娜:这本书稿最初是作为一个课程来写的。几年前我的好友翟鹏霄女士想做一个关于女性成长的课程,我们讨论起来,她就提到一个话题:女儿和母亲的关系。
很多人讨论女性成长问题是从性别视角出发的:男性和女性的经历和处境有什么不同,所以女性应该怎样成长一类的。但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个人生活层面,女性到底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她们已有的成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答案恐怕是在母女关系中:很多女性是跟着自己的妈妈成长起来的,她们的性格和行为模式里面的很多问题,是在和妈妈的关系里形成的。
这本书得到了一些读者的热情反馈,印象最深的是豆瓣上一位读者,说这本书主要是讲异性恋中心视角的母女和家庭关系,如果能再添加其他类型家庭的母女关系例子就更好了。
我很赞同这个反馈,现在回过来看这本书,这的确是个遗憾:我只写了我最熟悉的母女关系类型,即男权社会下一夫一妻制家庭中的母女关系。如果扩大视野,我们应该能看到更多形态的母女关系,而且其中恐怕会有不少,比我们平时常见的母女关系类型更健康。比如我就一直很好奇摩梭族母系社会中的母女关系。
采写/何安安
编辑/张婷 王青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