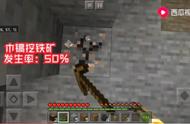作为一个嗅觉的天才,格雷诺耶自己却没有任何气味。从一出生,他的生存本能就压过了爱的需求,能够给予他温暖和爱的母亲必须死去,他才能存活下来。因此,对格雷诺耶来说,爱站在了生存的对立面。一旦他试图表现或体会到爱,死亡就会如影随形。童年时代的创伤导致了他在建立自我意识方面的病态和缺失。格雷诺耶试图用萃取法提取和保留某个实体的精髓的举动,可以看成是他无意识地想要提炼出一个“个体身份”的尝试,而这种尝试,与战后德国试图重建一个正常化的国别身份的意图,也不能说毫无关系。

或许正是由于纳粹文化对视觉符号的盘剥,作者才选用了“嗅觉”这一元素作为格雷诺耶自我认知的途径。考虑到1984年小说连载期间,西德导演埃德加·莱兹拍摄的史诗电视剧《故乡》创造的的收视狂潮,小说结尾处“还乡”情节的设置,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战后德国文学与电影中对“故乡”这一主题的重视。借由艺术的手法去呈现熟悉的、能够让读者和观众产生共鸣的故土的一切,以此重新认识和确立自己的个体处境。然而,在当时的德国,这种方式又难免陷入虚无的困境。

在现代理性对“自我”的认识中,驱动个体发展的核心动力是要去掌控、操纵并主宰自然界的一切,从而构造一个由理性推动的世界。格雷诺耶从一个本能追随气味的幼儿,到一个熟练的制香师的过程,对应的正是这种对知识的操控和驾驭。讽刺的是,掌握这种主流语言并不能够为他打开足够的生存空间。正如人类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体味,认为过度浓烈的个人气味是不文明的体现,嗅觉也往往与人性中动物性的一面联系在一起,而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对理性文明的追求,本质上就是相悖的。

除此之外,他的制香技术的成熟恰好对应了艺术从古典到现代,直至沦为文化工业商品的过程。虽然香水能够为使用者提供快乐和满足,却无法为制作者本人提供慰藉。当格雷诺耶成为气味王国的主宰时,他也把自己从这个完美的、自我驱动的闭合体系里剥离了出来,因而只能走向自我的毁灭。格雷诺耶冷酷无情的工具理性导致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病态,而这正是现代社会中无可避免的问题。他的孤独、焦虑和虚无深刻地揭示了个体在理性驱动的物质社会中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