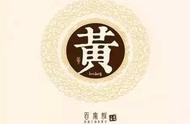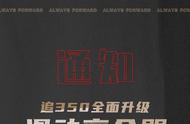张岂之
夏商周的法律制度包括“礼”和“刑”两个方面。三代强调礼治,特别是西周,形成了完善的礼乐制度,用礼制来区分贵贱,明确等级,维护统治秩序。同时,以惩处为中心的刑罚制度也已经形成。但是,这一时期的礼和刑尚未融合为一个体系,而是各自为用。礼主要用于调整贵族内部的社会关系,刑主要用于控制社会下层劳动人民。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按照史籍的记载,夏有“禹刑”,商有“汤刑”。西周的礼制和刑罚资料均较多,礼有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礼;刑有墨刑、劓刑、刖(髌)刑、宫刑、大辟五刑。五刑的具体条目,有三千种之多。1976年在陕西扶风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有一个刖刑奴隶守门鼎(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是西周刑罚的生动写照之一。
春秋时期(前770—前475),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据鲁《春秋》记载,从公元前722年到前479年,诸侯朝齐晋楚者达33次,而朝周王者仅3次。在诸侯国中,有实力的大夫控制了政权,如齐国的田氏,晋国的韩赵魏氏等。春秋后期,以郑国子产“铸刑书”(前536)和晋国赵鞅“铸刑鼎”(前513)为标志,法律制度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刑罚体系开始向成文法制转变。
经过春秋时期的演变,到战国变法以后,与君主集权制度的建立相适应,法家思想在三晋兴起,并在赵、魏、韩和秦国得到了广泛贯彻,通过变法,这些国家建立起以刑罚为主体的成文法律体系。如魏国李悝所作的《法经》六篇就是其中的代表。特别是秦国,在商鞅变法中继承了李悝《法经》的思想,改法为律,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策。此后,秦国统治者不断增加法律内容,其立法和执法的严苛和细密,在中国历史上是屈指可数的。
在法律制度上,秦代崇尚法治。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批秦简,反映了秦统一前后的法律状况,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仅仅从秦简涉及的秦律名称就可以看出,人称秦律“密于凝脂”是毫不过分的。秦简中的秦律,涉及政治、军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市场管理、货币流通、交通运输、行政管理、官吏任免、案件审理、诉讼程序等各个方面,“皆有法式”。在法律的实施上,秦代坚持轻罪重刑,严刑酷法,仅死刑就有车裂、定*(溺死)、扑*(打死)、磔(分裂肢体)、阬(活埋)、斩、枭首(斩头示众)、凿颠、镬烹、抽胁、腰斩、囊扑等方法。法网过密导致了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并成为秦王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初,以亡秦为鉴,废弃了秦代法律的严酷繁杂成分,由萧何制定了崇尚宽简的《九章律》,约法省刑,简易疏阔。张释之任廷尉,确立了执法不阿君意的原则,到武帝即位以后,伴随统治思想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重用张汤和赵禹“条定法令”,刑律日繁。“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汉律的形式,主要有律、令、科、比四种。律为律条,令为诏令,科为法律适用,比为案例类推。汉律强调皇权至上,法自君出,即廷尉杜周所说的“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但同时又强调法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有了“刑狱”和“诏狱”的区分。其法制的指导思想则为礼法并用,以礼入法,儒家经义成为法理的基础,坚持德主刑辅,先教后刑,奠定了此后法制体系“礼刑一体”的基本框架。近代严复曾说:“三代以还,汉律最具。吾国之有汉律,犹欧洲之有罗马律也。萧相国明其体,而张廷尉达其用。”在刑罚种类上,汉代逐渐以徒刑、笞刑和死刑取代了以前的黥刑、劓刑和斩左右趾,废止了部分肉刑,反映了司法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有一定发展。魏明帝时命陈群等人在汉律的基础上制定了《魏律》十八篇,将汉代的“具律”改为“刑名”,并列为首篇,这种体例一直被后代所用。西晋泰始三年,由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大规模修订法律,以汉律和魏律为基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制成了简约、规范的《晋律》二十篇。同时,由明法掾张斐为《晋律》作注,诏颁天下,作为有同等效力的法律解释。南朝基本上沿用晋律,变动不大。北魏在孝文帝时广泛总结汉魏晋法制的经验,修成北魏律二十篇。陈寅恪评价说:“北魏前后定律能综合比较,取精用宏,所以成此伟业,实有其广收博取之功,并非偶然所致也。”并认为北魏法律影响深远,“汇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于一炉而冶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于隋唐,成为两千年来东亚刑律之准则也。”
隋唐时期,法律制度有着重大进展。隋文帝令苏威等人制定了具有继往开来性质的《开皇律》十二篇五百条。到了唐代,唐高祖令裴寂、萧瑀等人在《开皇律》基础上制定了《武德律》,并编纂了令、格、式,与律配套,开创了唐律的四种形式。唐太宗时,房玄龄、长孙无忌主持对《武德律》进行长达十年时间的全面修订,形成《贞观律》。“凡削繁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唐高宗时,又由长孙无忌、李、于志宁等人编纂《永徽律》,同时还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统一注解,附在律文之后颁行天下,具有同等效力。后世将《永徽律》与注疏的合编本称为《唐律疏议》,看作唐律的代表。另外,唐玄宗在开元年间还主持编纂了《唐六典》,被后人誉为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典”,开了律典分野的先河。
唐律继承了汉晋以礼入律的传统,明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标志着礼制法律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唐律的法律形式也已经相当完备,律、令、格、式各有其用。“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在刑罚的类别上,经过汉魏的演变,至唐代形成了新的“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其中笞分五等(十至五十),杖分五等(六十至一百),徒分五等(一年至三年),流分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分两等(绞、斩)。在法律的实施上,唐代统治者强调慎狱恤刑,特别是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有效防止了滥用刑罚。
唐代在法制监督上有了新的进展,沿用了汉晋以来的御史台建制,以御史台总管监察。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分负其责。侍御史主要监督司法,推鞫狱讼。殿中侍御史主要监督殿廷礼仪,京城巡视。监察御史主要分巡地方,弹劾官吏。在司法监督上,大理寺初审,刑部复审,御史台监督,合称“三法司”。法司判决有称冤屈的,则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和监察御史联合审理,称“三司受事”。御史台监督的重点在于纠察百僚,肃清吏治。
宋代法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律,宋太祖时,由窦仪主持编纂了《宋刑统》,内容与唐律大体相同,没有超出多少。其中旧律规定不足者以及随着时代演变而出现新的法律问题,则用敕令解决,以编敕方式不断增补。“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这样,编敕就成为宋代特别是神宗以后更为重要的法律渊源。在司法实践中,“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同上),敕律并行,神宗以后,发展到以敕代律,并把唐代法制形式中的律令格式改为敕令格式。皇帝随时发布的敕令地位超过了相对固定的律条,反映了皇权在立法领域的强化。在刑罚种类上,增加了凌迟和刺配。
辽金元法制建设的成就不如唐宋,带有一定的原始性。“金初,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此可施诸新国,非经世久远之规也。”金熙宗以后,陆续颁布了一些律令,但较为零散。直到金国晚期的章宗泰和年间,才制定了较为系统的《泰和律义》,其内容大略不超出唐律。元初本无法律,断理狱讼沿用金律。忽必烈即位以后,逐渐开始法制建设,陆续制定了《至元新格》等条文。到英宗至治三年,修成《元典章》与《大元通制》两部法典汇编。《元典章》在体例上仿照《唐六典》,收集了从元世祖到英宗的诏令、判例及典章制度。《大元通制》汇辑了元世祖以来的“法制事例”,分为诏制、条格和断例三种。元代法律为一事立一法,缺乏系统性,而且均为现行规定,强调“古今异宜,不必相沿”,不取唐宋旧典。具体案件的决断,则以具有蒙古民族色彩的断例为主。在刑罚种类上,元代大量恢复了肉刑。
在法律制度上,明清是一个体系。洪武三十年,明太祖主持制定了《大明律》三十卷,首列名例,次按六部分类。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又制定了《大明会典》,作为行政规范性质的法典。正德、嘉靖、万历时对《会典》进行了多次校刊增订。流传至今的《大明会典》就是万历续纂本。清朝顺治四年,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体例内容基本同《大明律》相仿。康熙、雍正、乾隆时对《大清律例》不断修订,到乾隆五年定稿。今天看到的《大清律例》就是乾隆本。康熙开始,仿照明会典编纂《清会典》,其后屡次增订,形成了《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事例》《光绪会典》五部会典。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还制定过《回律》《番律》《蒙古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和《苗例》等针对少数民族的单行法律法规,以适应不同民族地区的司法需要。
随着古代法制的发展,到了明清,“例”越来越重要。由于明太祖强调“祖制”不得更改一字,在法律实施中为了弥补《大明律》的不足,从明孝宗时开始用“条例”和“事例”辅助法律。后来,由“以例辅律”发展为“以例破律”。清代继承了明代编订条例的做法,在编制《大清律》时就附有条例,康雍乾嘉道咸同光每个皇帝都增订条例,由此决定了清代司法中“例”占具优先地位,有例从例,无例才从律。而各种条例越来越繁复,这就给司法留下了极大自由裁量空间。在刑罚种类上,明清在杖、徒、流、绞、斩的基础上,增加了充军(流刑附加刑)、发遣(配边远驻防军人为奴)、枷号、凌迟等罚则。明清两代在司法的宽严程度上大不相同,大体上,在对官吏的法治监督上明代失之严峻,清代失之宽容。
明太祖惩元之弊,以重典酷法治国。在《大明律》之外,还专门制定了《大诰》作为司法依据,使“诏狱”制度化。在司法方面,古代向来都有诏狱,即由皇帝诏令在法律之外处理案件,判决不是根据律条而是根据皇帝的意旨。明初朱元璋处理的胡惟庸、蓝玉、郭桓、空印四大案,是诏狱的典型案例。胡案和蓝案对功臣大开*戒,株连四五万人,将元老宿将一网打尽。郭桓案是借口户部侍郎郭桓贪污惩治京官,六部长官多数被*。空印案是怀疑地方到户部核对钱粮的空印文书有弊,将府州县主印官员以及部下*头流放。另外,明朝还创立了廷杖之法,对敢于抗命的官员当廷杖责,打得皮飞肉溅甚至死于非命,相当多的正直之士遭受过这种屈辱。这些做法,打掉了多数官员的廉耻和自尊。法网稍一松弛,吏治立刻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尽管明太祖自己也曾说过:“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谓善治乎?”然而,重典治国,法外用刑,正是由明太祖奠定的明朝法治基调。
清代司法,强调“以德化民,以刑弼教”,一般较为宽松。即使人称暴戾的雍正帝,其残暴冷酷,主要表现在与“夺嫡”有关的宫廷斗争上,而在治理国家上则循法守规。但是,出于满汉隔阂,清朝整饬吏治从宽,整饬思想从严,对官员司法以宽大为主,对文人司法则以严酷出名,大兴文字狱,在思想文化的专制上走向了极端。
在法制监督上,明清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并将六科在名义上改归都察院管辖,从体制上完成了台谏合一,使其成为法制监督最重要的机构。都察院的最高长官为都御史,执掌纠察司法,大狱重刑则会同刑部、大理寺共同鞫讯,称为三司会审。三司会审不能决断者,则交由九卿会审。吏部考察官吏,由都察院监督。都察院下辖科道,但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相对具有较大独立性。监察御史按省分道,分别负责弹劾官吏,巡视京城,刷卷(审核文档),监督科举,巡查仓库,纠察礼仪,上书进谏,巡按地方。给事中按六部对口设置,分别负责审查对口各部的奏章文书,监督部政,驳正违失,进谏议政。六科未签署的公文,六部不得执行,六部有事,堂官要赴科画本(签署)。清代都察院与明代作用类似,所不同处是根据省份的变化改十三道为十五道。科道的强化,使古代的监察制度发展到高峰。
秦汉以来的法制,以皇权为法律的基本渊源,刑法、民法、行政法诸法合一,司法行政不分,形成了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明清的法制体系,把中华法系推到了尽头,却缺乏向近代法制体系转化的内在机制。到了晚清,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冲击下,逼迫统治者对法律条文做了一些修改。但是,最终也未能走上立法民主化、司法独立化的近代化道路。
中国古代的政治、选举、法律制度,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极为丰厚的内容,并且在历史演变中具备了高度的自洽性,能够不断自我修复完善并自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的制度体系,可以对包括皇帝在内的人的因素形成一定的制约,同时又能激发人为改善制度的不断努力。从技术性和操作性上看,古代的这一制度体系,比较有效地维持了统治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在统治集团中吸纳社会精英,形成较高素质的官僚队伍,其中有些方法和措施,如政府机构的权力配置与相互制约、科举选官的操作方式等,已经达到了非常精致的程度,不乏有可供现代参考借鉴的成分。作为传统社会遗留给今人的一份遗产,其历史作用和借鉴价值已经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政治制度方面,三代形成的礼制,确立了古代政治的价值取向;秦汉形成的帝制,构建了王朝时代的体制框架。秦汉以后,国家机构的“秦制”和文化传承上的“周制”经过不断渗透磨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一方面是君主集权,保证大一统国家的稳定运行;另一方面是君主也要受天命、祖宗成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的制约。以文官为主体的官僚制度,与皇帝制度相配套,实现了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的高度吻合。在选举制度方面,由世卿世禄制,到军功、察举制,再到科举制,不但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而且推动了古代的社会流动,使封闭的社会等级具备了一定的开放性。在法律制度方面,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华法系,具有鲜明的特色,以礼法并用的方式,把“天理、人情、国法”有机融合在一个法律体系之中,保证了传统社会的治理秩序。
不过,中国古代的这一制度体系,在整体上是同皇权专制的“家天下”体制相适应的。专制体制的人治本质与制度规范的法治要求,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冲突。因此,中国古代的制度,与现代民主制度有着本质差异。对于这种制度体系的本质和弊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指出:帝制时代的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是传统政治制度的根本弊端,“为天下之大害”。三代以后的法制,“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中国古代的这种置天下于一家之“筐箧”的专制性质,使其制度建设更多地侧重于保证君主的绝对地位,保证政治统治的有效性,而对社会管理重视不够,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一治一乱的王朝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