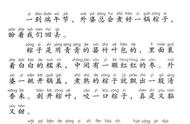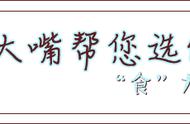今天读汪曾祺的散文《炒米和焦屑》忍不住也想写写小时候我们的零食。汪曾祺写他家乡的炒米“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家常预备,不过取其方便。用开水一泡,那就可以吃。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泡一碗,可代早晚茶。来了平常的客人,泡一碗,也算是点心。”
这个炒米正如汪曾祺文中所说“炒米是各地都有的”,我们海南也是有炒米的。
我们的炒米一般是下半年稻谷丰收时节。新稻谷割回来,放到大锅里煮。煮熟晾干再拿去脱粒。脱粒好的米用陶罐子装好,等着天气微冷了就可以炒了。
炒米很简单,但炒得好吃那就需要技术了,大灶炒出来的要香一些。把锅烧热,然后倒入适量的米,不能放太多,太多了翻炒不及时有些会焦,也不能放太少,太少了锅会烧坏。
锅热倒入米要要不停地翻炒,这里的翻炒不是拿锅铲。大人一般是用手掌,手掌打开不停得抚摸米粒,动作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要让每一粒你都能贴着锅壁,才能让米爆开。那个时候总觉得每个大人都是武林中人,会铁砂掌。而我们孩子自己炒就拿小炉,小锅,筷子来翻炒。
我最喜欢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老人说声音响得越清脆,炒出来的就越好吃,证明这是炒全爆了,也证明这个新米煮饭也会很出饭。
炒米出锅我们要装到一个玻璃瓶里,必须是有那种拧的盖子的。而且这个玻璃瓶要用纸巾擦拭干净,不能有水。炒米受潮就软了不好吃,不脆了。
一般一次就炒吃个三四天的,有时一天就被我们吃完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南方的炒米就相当于北方的爆米花。就是大人小孩嘴里嚼着的那零食。
冬天上学的时候,早上装两个校服兜满满两兜。下了早读,三五成群结伴聊天时就会问“你带炒米没有?”。谁带了每个人在她兜里抓一把,边聊天边嚼,那个味道满嘴飘米香。那个时候瓜子都没有炒米畅销。
炒米不单可以炒好了吃,还可以做成其他的零食。“爆米糖”“花生爆米糖”“花生芝麻爆米糖”。这些做工和材料要多一些,一般是春节前几天做,做来当年货。拜年的时候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摆在茶几上,那是会被笑话的。
爆米糖的做法不难,炒米好倒出来,放红糖和白砂糖到锅里炼,达到粘稠了就把准备好的炒米,花生芝麻等等材料放到糖液里搅拌。然后倒出来在米筛里,大人用手沾水整个手掌把它压平。等凉了就可以用刀均匀地切成小块装到玻璃罐子里。
越长大离这些零食越远了,现在随处可以买到,却吃着不是那个味道了。现在想来或许炒米也好爆米糖也好,可能真的没那么美味,只是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年代,它就显得比较珍贵和美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