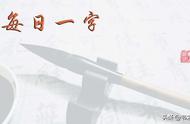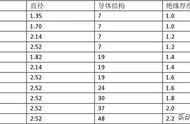文/图:远心
1



我小时候经常猜想,我出生的村子为什么叫“灌城”,灌字好奇怪,难道是灌水的城?因为总被淹?
我记事起,每年西大洋水库上涨,娘总是一大早天不亮就去抢收粮食。水库边的地水大,一旦春天水位下降,地露出来,好好的地,大家就忍不住种上麦子、黄豆。盼着也许今年淹不了呢,也许多少能收点。结果,年年麦收前,水位说涨就涨,人站在水里收没有长满的麦穗,快要成熟的黄豆。穿着水鞋,深一脚浅一脚的。水虫子在水面上飞。
那时候我望着浩渺无边的水库,真是又怕又恨。水是清澈的,而庄稼地的泥是软的,到处是泥水。涨得快起来,一会儿就漫过一片地。我娘是干活使蛮劲儿的铁姑娘出身,经常气的留着泪。镰刀、筐、一身泥和着眼泪,混合在水淹地里。
我是和娘一起亲自感受过这些过程。所以,我对水库,一直是爱恨交加。我一直不知道它的边际,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
只知道夏天三伏天女人们去游泳,孩子在水里开心打闹。我一直没有学会游泳,总是害怕。只要感觉到水超过身高,立刻掉下去。我的狗刨,停留在刨十米八米的水平。
娘是朱家庄的,离水库远,她不会游泳。大概就因为她不会游,我一直没有放下对水的恐惧。奇怪的是,在某一个炎热的夏季,在离我家院子一公里左右的水库边,我突然学会了仰泳。确切地说,我突然能躺在水上了,平平地,把身体放在水上,手在两侧,脚轻轻一动,就走了。狗刨那么费劲儿也走不了几步,仰泳却很快就能走得很远。
我躺在水上,望见了西边那座高高的青山。我在那座山脚下出生。望见了水库边高地上绿油油的庄稼地,水上碧蓝的云天。我如小鸟般轻盈,被水托起来,如果有翅膀,一定展开翅膀,飞到空中去。
2


三四年前夏天,回到灌城村随娘小住。同学们开车带着我,到唐县,爬青虚山。一路之上,我才第一次听说了灌城的来历,灌城——灌婴城。
百度百科呈现:
灌婴城是指河北唐县罗庄乡灌城村,位于唐县西部,东临西大洋水库。原为灌城乡政府所在地,后1996年与伏城乡合并新建罗庄乡。秦末汉初名将灌婴在跟随高帝攻打陈豨的时候,受皇帝的命令单独在曲逆(注:曲逆,古地名。秦置,因曲逆水得名。故城在今河北省顺平县东南)一带攻击陈豨丞相侯敞的军队,大败敌军。当时所建的屯兵驻扎的城池被后人命名为灌城,旧址现位于西大洋水库水下。逐渐的在此地形成了村落,靠近该地的村即为灌城,城池外屯兵的村则为东屯村,南屯村,西屯村,北屯村。
1958定于在此地修建水库,各村搬迁至山脚地势高的地方,至此旧址随着水库水位的涨落在人们眼线中出现。同时由于历史的沉积旧址已为人们利用,做为耕地使用。至今村中仍有西台、南台(相传为当时的烽火台)等地名。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道路只能通至该地,无法发展有效的经济产业,目前处于较落后的情况。
这一段,用语成熟,明显是经过锤炼的文字。但是,并没有指出灌婴城的文献出处,还需要历史记载和文物考证双重支撑。
当我知道灌城是灌婴城的时候,着实一惊。我小时候总是感觉我们的村庄比周围有所不同,我们村的人好像比别的村更有气质,更注重念书,村子也较大。虽然总是被水淹,但是我们村儿背山面水,比那些离水远的村子明显多些灵气。这种感觉或许也是灌城村人共同的优越感,我不知道这优越感从何而来。
如果真如这段文字所言,此地曾是灌婴驻扎屯兵之城,那么大的汉朝将军,后来是做了宰相的,我们村儿不至于这么默默无闻吧?可如果不是,为什么叫灌城?
我猜测,也许灌婴确实在此驻扎过,打败敌军后很快撤离。留下人驻守,渐渐地,这座城池周围,有了村民,形成了村落。
刘邦手下将领灌婴,汉朝的开国大功臣,官职升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汉代丞相,为人以骁勇而闻名于世。如果真是灌婴驻扎之处,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到1958年修水库,这座两千多年的村落,就被埋在水库底。
还有谁记得我们的村庄?我们的旧村儿哪儿去了?那时过得是什么光景?这些疑问,涌上心头。
3

我爷爷总是讲,早先里时候,旧村里时候……爷爷2010年初猝然去世,我带着一岁半的女儿回到灌城,面对苍茫的水库,感觉到人事无常,唯留一片空旷。我童年的村庄,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一个有戏台的村庄。每年四月初八,是大庙会,前后一周,会请县城大剧院,甚至保定大剧团才唱戏。90年代左右,小时候,搭棚唱戏,长条板凳一个接着一个,老人、孩子,男人女人们,大家都挤在一起,看戏台上完整的大戏。河北梆子多,也有评剧,老调。我家离大队戏台大概不足200米,我晚上,经常在大戏的梆子锣鼓声中入睡。戏台上生旦净末丑,悲欢离合,在童年的梦里,也会一一浮现。
我爷爷常常带我去看戏,看完戏后,拿着手电,照着黑压压的乡村小路,一前一后回家。头上的月亮,映照着东边的山梁,夜晚的山好像能通天。静静的长长的乡间小路,好像蕴含着世间所有的奥秘。
爷爷离世,旧村的历史,我还没来得及问清,他反反复复说过的那些话,像断线的珠子,滚落在时间之外,好像怎么捡,也捡不回来了。
您爸爸知道旧村的历史吗?坐在闺蜜张英家的沙发前,我问她老公刘波。那怎么知不道啊,你问问他,年年就跟俺们说,说了多少遍了都。刘波的话,让我想起我爷爷。当年也是这样,他一说早先的事,我爹就这么说,可当年究竟如何,他离世后大家竟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原来也是一次又一次重演。我们就在那样的重复和忽略中,遗忘所有的记忆。
刘老师1953年出生,叫刘军起,1958年修水库开始搬家,他已经开始记事了。
他说怎么不记得啊,那年发大水啊,雨一直下,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不停。旧房已经拆了半边,墙和房顶都开着,就剩下炕儿头上那一块儿,上还有一块房顶。俺们家里四五口人就挤在那个炕角,在那儿避雨。我当时六岁,也不知道怎么就跑出来了。水都齐腰深了,我就开始跑,从旧村往新村跑,雨下着,我吓得啊,跑到现在村里那个大商店的位置,一个人儿都没有,我开始大哭。
这一幕,经过两次描述才说完整。一个六岁的男孩从拆掉的被水淹的家,从下雨涨水的旧村,向上跑,跑过村子里变成废墟的房子,跑过漫过村庄的洪水,跑过恐惧和求生的本能。那就是搬家行程中一个最有象征意味的行程。那一幕,永远留在刘老师心里。
你还记得旧村的样子吗?记得啊。能不能画出来?我画不出来,有人能画,比我记得还清楚,你等着,我给你打电话叫。说起旧村里可有几个记得清的,正好回来过年来了。
人还没来。我拿着一张纸,东南西北标上,他开始给我叙述记忆里的灌婴城。
村东里有一个牌楼,写着咱们村的名字。从牌楼大门里进来,往西一走村里最显要的位置,就是俺们刘家,占了一条街。东北那块是姓刘的。南边有个南台子。走到村中间,有一条南北路,从北边的唐河河沿一直通到南边。南边有个庙,叫什么名字俺记不清了,有一棵几百年的老树。中间再往西,就是你们赵家,西北边是高家。灌城就这四大姓为主。北边挨着河沿,是紫禁城,就那么叫,也就剩下老城墙了,挺长的一段。城墙往西是一道大深沟……整个村子都在唐河北岸,那时候唐河就从村西流到村北,从十八渡、东庄湾,流过灌城,流到北屯、南屯去。
我们大概画出来。
我被这张图吓了一跳。
这真是将军驻扎的气度啊。不知驻扎了多久,修了紫城墙,北边还有炮台。
2019.2.5 23:26今天初一,见了很多人,了解了很多过去的事儿,先写到这儿,以后再往下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