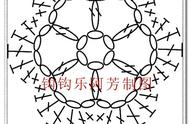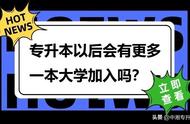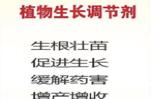但需注意的是,城市文化从不是静态标本——开埠后的上海本就是移民与本土交融的产物,弄堂里曾有苏北话与宁波腔的混响,国际饭店的咖啡香气与城隍庙的油墩子并存。所谓的“传统”本身便是不同时代“新潮”层层累积的结果。

空间重塑的经济逻辑
武康路、安福路等街区的网红化,本质是资本对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旧租界建筑因其历史风貌成为消费符号,吸引创意产业与年轻中产入驻,形成“生活方式经济”。这种更新虽带来活力,却也导致在地社区的解体——原住民因租金上涨被迫迁离,市井商铺被连锁品牌取代,形成“橱窗式的怀旧”。

代际审美的断层与缝合
年轻人对“新潮”的追逐,实则是用Z世代的表达重构城市记忆:咖啡馆取代老虎灶,快闪店置换烟纸店,但打卡行为背后仍是对“海派风情”的另类消费。矛盾的是,当“复古风潮”将百乐门舞厅变为沉浸式剧场时,怀旧本身已成为一种时尚商品。

实体空间的消逝与记忆载体的转移
石库门成片拆除的同时,田子坊、建业里通过商业化改造延续建筑外壳;本帮菜馆在米其林榜单上与网红brunch共存。传统并未消亡,而是以碎片化形态嵌入新语境。老一辈的“消失”焦虑,实则是私人记忆与公共空间错位的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