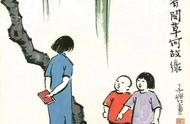吃完饭,跟奶奶打声招呼,出了厨房,来到院里墙根下,一片亮白还显橘黄的阳光下,放着三弟刚从卧室端出来的一张方凳,凳面上放茶壶一个,已经冲进开水的茶壶嘴,像焚香一样,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在黄土墙的背景下,像宣纸上洇开的国画笔触一样,渲染铺展开来。茶香在壶里酝酿,在壶盖处喷涌。三个洁白润亮的茶杯在阳光下流离着光晕。

阳光正好,时间恰当,饭后晒晒太阳,喝上一杯热茶,抽上一根烟,闲谝话家常,与小弟开着儿时大人与我们开过的玩笑。自离家出走那天,匆匆几个月,从来没有如此缓慢节奏,舒舒服服的吃喝一顿。奶奶忙完厨房里的活儿,手里攥一把大葱走了过来,坐在我们旁边,开始择菜。小超弯下身子,和奶奶小声聊着。问着她的身体状况,埋怨她不停歇的干活。她悠悠缓缓的述说着家里近来发生的事。安宁,平静。悠闲自在的时光里,某种叫幸福抑或快乐的东西,突袭而来,让热火的闲谝忽陷停顿。我靠着椅子背,眼睛直直的望着头上一片深邃湛蓝的深冬天空,眼泪像夏时的树胶在眼眶聚集,饱满后,从眼角滑出,顺着两鬓,灌进耳朵。小超和建伟一样,以不同的姿势在发愣。我们集体陷入了沉思。幸福感过后,某种对它突袭而来的自然反思。奶奶起身,边走边说,中午吃大葱白萝卜馅的饺子。
喝完茶,我们仨商议着去村里转转。家里抽烟毕竟不方便,怕被大人看见,又一顿说教。

时过中午,太阳当头,阳光正猛,一幅暖春景象。走在巷弄土路,向阳处,一会儿就觉得燥热。内衣里的虱子也活泛起来,顺着旧有路线和暗道急行军。我们仨一身正常人的衣着,可衣服里面,正危急难耐。人多处,我们尽量避免,怕挠痒痒的动作让人起疑,毕竟那年头还生虱子已经不是正常事了。小超带我们在灌溉的渠沿上遛弯。绿色麦苗,整齐划一,巨大的长方形状,延展向南而去。渠沿上杂草枯黄变干,一脚下去,粉身碎骨的声音后,一地齑粉。渠内堆满垃圾,苹果的塑料膜袋最多。微风下,在渠内胡乱舞动飘飞着。有一段,积有雨水。水底黑色的淤泥,绿色的苔藓在泥里生存。虎尾草,毛刷似的种子在风里摇摆。野枸杞在渠沿的土基台上招摇,枸杞已无红宝石的色泽,干瘪如一粒粒红色的老鼠屎。野枣像一堆冬眠的刺猬挤在一起。紫褐色果实,落在枣刺丛里。细长芦苇,头顶芦花,风里诉说着冬的寒冷。一条田间小路上,几棵孤独的白杨树,在风中哗哗哗的响,叶子反射着阳光。一地枯黄,尸身满地的枯叶,厚厚一层,犹如地毯。两棵柿子树,在一片果园的地头,守卫战士一样,倔强的矗立着。遒劲的枝干,弯曲延伸,如挥毫在纸,笔笔如刀。远望,太白山余脉在蓝天下,深蓝如背景板上的画。

我们自东向西而行,漫无目的,心神懒散,走走停停。一颗石子,被我踢了一百多米,还在脚下。水渠拐弯向南时,我一脚结束了它的旅程,让它躺卧在水渠里,明年黄河水再来时,会带它再走新的旅程。
走下灌溉渠两百米不到,是小超上小学时的母校。学校墙外一排十几棵泡桐树,最粗的有两搂,最细的碗口粗,正在被砍伐。有的已被挖出树根。大的树根像一个小草垛子,垛顶一个树桩的截面。我们爬上树桩,坐在上面抽烟,我开始细数树桩上的年轮,像涟漪在水面荡开。一共数了十四圈,根据小学学到的知识,这棵树活了整十四年。十四年,小学要连上两遍的概念。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学校旁是村支部,村支部旁是乡村医生的药店,药店旁是一间小小的理发店。全部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土坯墙在唰唰的掉着泥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