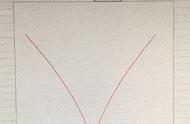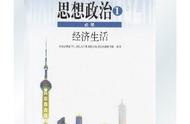哈利利所著《寻路者: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
关于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的学术,应该叫阿拉伯学术,还是叫伊斯兰学术,一直有争议。阿拉伯人占领了叙利亚和波斯之后,当地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阿拉伯语写作,在帝国早期,阿拉伯人相当开明,犹太人、波斯人、景教徒都不必改宗。按照哈利利的说法,凡是以阿拉伯语写作的都该算阿拉伯学术或者阿拉伯语的学术。当时的阿拉伯人掌握着统治的语言,这语言却没有承载内容,智慧宫的一位阿拉伯翻译家说:“我们掌握语言词汇,他们(波斯人)却拥有思想。”波斯人也不谦虚,他们甚至认为希腊的学问都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从波斯偷走的,然后烧了波斯的原著。
智慧宫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是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Abu Zayd Hunayn ibn Ishaqal-Ibadi,808-873)。他是景教徒,专业是医药,出生在希拉(Al-Hirah),即库法城,他会叙利亚语和波斯语,后在巴士拉城学了阿拉伯语,在亚历山大城学了希腊语。马蒙为了搜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派了一队学者到拜占庭求书,伊斯哈格应该位列其中。伊斯哈格翻译了大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他一般先把希腊语翻译为叙利亚语,再由别人(很多情况下是他儿子)从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他还把《旧约》译为叙利亚语。
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的儿子名为伊斯哈格·伊本·侯奈因,也是景教徒,除了翻译还做医生,一度接替他父亲主持智慧宫的翻译工作。他还修订、注释早期的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译作。正是靠了他的注释,阿威罗伊才读懂亚里士多德。智慧宫中有很多景教徒一点也不奇怪。在蒙古人出现之前,景教是最大的基督教分支。活动范围覆盖了从地中海东岸直到中国中原的亚洲大陆的大部分,阿拉伯帝国之初曾有两千万景教徒。旭烈兀的母亲,也就是托雷的老婆唆鲁禾帖尼(SorqoγtaniBeqi)是景教徒,旭烈兀的老婆脱古思可敦也是景教徒,本应嫁给托雷,但托雷在婚前死去,于是按照蒙古习俗嫁给旭烈兀。
早期的翻译者和学问家中有很多业余人士,所谓“民科”。他们中有医生、商人、货币兑换人(金融从业者),都是财务自由的人。最被重视的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数学书,托勒密的天文书,以及盖伦的医学书。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今天还与我们同在,但天文学家兼占星家托勒密的《天文大全》和盖伦的医学著作今天只有历史意义,没有科学价值。数学是永恒的;而科学是渐进的,有时可能还有革命。
现代科学史的奠基人萨顿(George Sarton)对数学史有独特的兴趣和见解,他的小册子《数学史研究》(The Study of History of Mathematics)今天看来仍然充满洞见。他称公元800年到850年这段时间为“花拉子米时代”,但早期的数学通史很少提及阿拉伯语文献。对阿拉伯语数学文献的重视程度是随着时间而增长的。1888年初版的鲍尔(Rouse Ball)的《数学简史》(A Short Account of History of Mathematics)大概是第一本用英语写成的数学史。其中把阿拉伯数学列为一章,印度数学只是这一章中的一节,这是为了阿拉伯数学做铺垫的。鲍尔把花拉子米的英文名字翻译为Alkarismi。1893年出版的卡约里(Cajori)的《数学史》中则有“中世纪”一章,第一节讲印度,第二节讲阿拉伯,第三节讲阿拉伯数学回传欧洲。卡约里还把阿拉伯人叫作“撒拉逊人”。这些早期数学史著作压根都不提中国数学。
数学史家贝尔(E. T. Bell) 1961年出版的科普读物《数学大师》(Men of Mathematics)一书按时间顺序记载大数学家的生平轶事,阿基米德之后,就直接到了笛卡尔。以霍金之名编辑的数学原文文集《上帝创造了整数》(God Created the Integers),在阿基米德和笛卡尔之间还加了个丢番图,但即使从丢番图到笛卡尔,也隔了一千两三百年。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但文明并没有因此止步。即使考虑到种族和宗教的隔阂,我们也不该忘记文艺复兴之前三百年的斐波那契吧,那可是意大利人啊,也许恰因为他的学问源自阿拉伯语文明,他的东西不被史家重视,对斐波那契的研究是近年来才兴起的。值得指出的是,丢番图的《算术》(Arithmetica)的阿拉伯语翻译是在花拉子米的书出版之后。涅尔夫妇的逻辑史权威著作《逻辑的发展》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然后就直接跳到了最后一位阿拉伯语哲学家阿威罗伊。1958年初版的斯科特(J. F. Scott)的《数学史》压根儿就没提花拉子米,只是在“东方数学”一章里,提到了几位印度数学家。

《数学大师》
美国数学史家博耶(Carl Boyer)1968年出版的《数学史》是经典,他由此被誉为“数学史家中的吉本”(Gibbon of math history)。博耶提到了花拉子米,但评价并不高。他认为花拉子米的表述是修辞性的文字表述,而不是严谨的数学表述,并且花拉子米不知道负数。他认为阿拉伯数学只是继承希腊数学,并没有太大发展。这和早期西方哲学史家对阿拉伯语哲学的看法类似。
伊夫斯(Howard Eves)的《数学史导论》在1981年出到第五版时仍然对阿拉伯人于数学的贡献犹疑不决。他提到了花拉子米,但没有仔细分析花拉子米的著作,只是把从阿拉伯语黄金时期从花拉子米到海亚姆发展出的代数,统称为几何代数,因为他们关注用几何求解代数问题。1972年出版的克莱因(Morris Kline)的大部头《古今数学思想》对花拉子米的评价就更加客气一些。但克莱因认为阿拉伯人对数学并没有在印度人的基础上推进很多。克莱因受博耶的影响很大,他的史料几乎都来自博耶。
倒是数学家或者数学家转行的数学史家对花拉子米赞赏有加。丘成桐最近研究近代数学史有心得,他鼓励岁数大的数学家研究数学史,他直言中国数学史家的著作中有义和团元素。他认为贝尔的几本数学史写的不错,但不够深,他夸赞韦伊(Andre Weil)的那本经典《数论史》,其实那本书是把数论的硬内容和有趣的数学史揉在一起讲的。最近出版的杜索托伊(Marcus du Sautoy)的《素数的音乐》是科普版的《数论史》,但角度清新,非常可读。杜索托伊才五十五岁,他前两年刚接手道金斯曾担任的牛津西蒙尼(Simonyi)科普教授席位,自己也爱写科普。日本大数学家高木贞治的《近世数学史》也相当引人入胜,日本人的文笔诚恳而简洁,用来写数学真是恰当。当然,由数学家退休或半退休后改行的数学史家肯定属于被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自辩》中嘲讽但同时又是心酸而无奈地叹息的“不能研究数学,只能八卦数学”的人(writing not mathematics but “about” mathematics)。但数学家们写的“八卦数学”的作品普遍比非数学出身的数学史家的作品更有洞见,毕竟是内行说史。

《素数的音乐》
麻省理工的数学家斯特罗伊克(Dirk Struik)的《简明数学史》尽管篇幅不长,但却是一本可以和博耶的《数学史》比肩的著作,这书1987年出到第四版,但1948年出第一版时作者就详细介绍了花拉子米的工作,是较早重视阿拉伯数学的。这书的初版在北平法文图书馆曾有收藏,解放后辗转到了中科院图书馆,只在1951年5月4日被借阅过一次。斯特罗伊克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自称他的数学史研究方法是社会的。这个方法用到阿拉伯黄金时期的文明倒是恰当。左派在数学家中并不少见。斯特罗伊克是荷兰人。范德瓦尔登的老师之一曼那瑞(Mannoury),以及曾任托洛斯基保镖的逻辑学家海恩诺特也都是荷兰共产党人。斯特罗伊克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受到迫害。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援引美国宪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非美委员会的所有问题。他被剥夺讲课权利五年,但慷慨的麻省理工学院支付了他五年全额工资,直到1956年才重新恢复教职。他老人家长寿,2000年以一百零六岁高龄去世。麻省理工对待斯特罗伊克,表现得比当时其他学校逼格高,这也体现在1960年代对乔姆斯基的保护上。但当时的麻省理工校长确实宣读了对斯特罗伊克的谴责。2000年他死后,学校撤销了当年的谴责,但没有道歉。学校沉默地辩护学术自由,教授沉默地接受。
差点变成职业音乐家的菲尔茨奖得主高尔斯爵士(Timothy Gowers)主编并有一百三十三位一线数学家参与撰写的《普林斯顿数学指南》(The Princeton Companion to Mathematics)是一本独特的数学读物,这本大书花了高尔斯很多精力,他亦引以为傲。天才数学家陶哲轩高度赞扬此书,说它既不像百科全书,也不像综述,也不像科普,但它是一本极具价值的参考书,对内行外行都有用。这本《指南》的第六部分是按时间排序的数学家传记,从毕达哥拉斯开始到布尔巴基结束,在阿基米德和笛卡尔之间,多了几位,其中就有花拉子米、斐波那契和卡尔达诺等。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花拉子米。现在流行的标准数学史教科书对东方数学的评价更加公平。卡兹(Victor Katz)分别在2009和2014出版《数学史》和《代数史》。两书都在希腊和中世纪欧洲数学之间分别加入了三章,一章讲中国,一章讲印度,一章讲阿拉伯。

Timothy Gowers
*******
文艺复兴之前的一千年是西方的黑暗时期。但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文明并没有断。科学史家莫勒(Violet Moller)的《知识地图》(The Map of Knowledge)干脆把中世纪知识的迁徙用不同城市按时间列出:亚历山大城,巴格达,科尔多瓦,托莱多,萨勒诺,巴勒莫,威尼斯。从这个角度看,文艺复兴的突发是一个伪命题。外在地看,文明的流动是个渐进的进步过程。内在地看,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维持的高水平所持续的时间也不如希腊或者阿拉伯文明的高峰持续时间那么长。
文明的体现是它的内容,而不是它所在的地域或者人口种族等载体。希腊文明从来没有中断,欧洲进入黑暗时,文明游离到了中东,载体是波斯人、阿拉伯人、景教徒和犹太人。后来到了西班牙南部、北非和西西里岛,主要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科学革命和文艺复兴先发生在意大利,是因为意大利和北非较近,贸易方便。尽管文明绕了一圈回到欧洲,但载体也不再是希腊人,而是曾经的野蛮人,再后来传播到更野蛮和荒凉的西欧和不列颠岛。
文明的每一次地理上的迁移,都会经历一次大的提升。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段,西方哲学史家并不认为阿拉伯哲学有原创性,只是把希腊哲学阿拉伯语化了,起了接力棒的作用。现在看,阿拉伯学问,除了希腊外,还吸纳了波斯和印度的学问,融会贯通后交给下一棒。早期西方学界更加亲近在时间上更远的近邻:希腊先贤。这自然会贬低地理上更远、而时间上更近的阿拉伯远亲。远亲不如近邻。法拉比(Al-Farabi)是阿拉伯世界一位自成系统的哲学家,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注释和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调和对后代阿拉伯哲学和西方哲学影响很大,被称为亚里士多德(“首圣”)之后的“亚圣”(Second Master或Second Teacher)。法拉比在那本百科全书式的《科学举要》(Enumeration of the Sciences)中,把知识分为几个类别:1)语言;2)逻辑;3)数学与音乐,这包括算术、几何、光学、天文、音乐、力学等;4)物理和神学;5)形而上学,道德和政治学。这明显传自希腊,今天的通识教育(liberal arts)也大致按这个传统。纳迪姆的《书目大全》尽管书目收录完整,但却没有法拉比那样对学科层次的洞见。
哈利利也是恨铁不成钢,他在《智慧宫》最后一章中讨论了为什么阿拉伯没有和现代科学沾边。这个问题在阿拉伯知识分子中,犹如李约瑟之问在中国。从文明迁徙的角度看,对李约瑟问题倒是可以有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回答:东亚离文明的中心太远,没机会加入文明的大循环。在动荡不安的年头,放大时间颗粒度,能够为人类取得的成就自豪,从而增添一些乐观的精神。
********
现代一元二次方程的表达式是 ax2 bx c = 0。花拉子米不知道负数,于是他给出了一元二次方程的六种可能形式,
1. ax2 = bx
2. ax2 = c
3. bx = c
4. ax2 bx = c
5. ax2 c = bx
6. bx c = ax2
这里a, b, c都是正数。花拉子米当然也不知道还有复根,其实现在的初中代数也不讲复数。
华裔学者罗博深(Po-Shen Loh)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数学教授也是美国奥数队的教练,他在2019年底给出了一个求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更简单快速的解法,曾经引起热议。把古老的东西玩出新花样,挺有意思。
有些人把花拉子米的代数贴了“几何代数”的标签,因为花拉子米的解用到了几何方法。拉希德不喜这种说法,他认为花拉子米不懂希腊文,肯定知道《几何原本》。花拉子米代表了波斯的数学传统,他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是反希腊的。后人对花拉子米轻视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代数书的目的就是实用,而不像希腊数学那么纯粹。后来通过斐波那契传到新欧洲的阿拉伯数学的主要是为了贸易记账。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自辩》中说数学家研究数学是为了美,而不是为了实用,大部分数学是不实用的。但我更喜欢物理学家尤金·威格纳(Eugene Wigner)的文章“The 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of Mathematics in Natural Sciences”,对自然科学,数学就是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