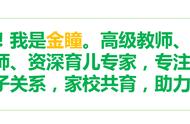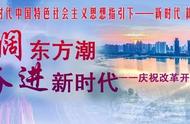春节前,有网友私信问:用我的书体,写“虚室生白”应该注意什么?我当时回答了几点,然后说有空我写一幅看能不能对他有丁点参考价值。
今天就贴出小作“虚室生白”,不过只是兑现一半承诺,为什么说一半呢?因为他问我的是楷书,我今天贴出的是隶书。作品还是没写落款,没上姓名章,只上了一方配合虚室生白意境的闲章,“莲心不染”。

我不是书法圈的人,我所有的重心是美学,尤其是中国传统美学,书法只不过刚好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对很多人来说,书法就是写几个字而已,瞬间搞定,所以,现在有那么多即席挥毫的活动,网上直播更是多不胜数。但对我来说,我无法即席挥毫,每次创作我都磨蹭许久,最后如果侥幸写出一幅还算满意的作品,多少有点像武林小说里说的运功过度后耗损不少真气的疲惫感。
这也是我只能发布每天一字,而不能每天发布一作品的原因,对我来说,一天的创作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写一个字,是练笔、写字,而不能算创作,而现在的即席挥毫,不管写多少字,也还是写字,而不是创作,创作需要更多准备。譬如,当我说了写虚室生白之后,在我的认知里,书法不仅仅是线条和空间的艺术,线条也应该跟书写内容融合。每个汉字都是有生命的,写一个静字挂家里,哪怕线条再好,但如果线条是非常跳跃躁动的,它也没有静的味道,也谈不上是好的汉字书法作品,除非创作初衷就是为了故意形成这样的冲突。
所以,首先要明白虚室生白的意思,事实上,我认为不管是创作者还是审美者,都首先要理解笔下文字的意思,才能更好地创作(审美)。虚室生白出自《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从历代学者解释来看,室是指心,空灵的心能生光明。而我们更要问的是,为什么心空能生明?以我一直认为道禅相通的立场,我觉得虚室生白跟一个著名禅宗故事说的是一样的。
那个禅宗故事就是,慧可说,老师,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就说,小意思,没问题,“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说,老师要心啊,我找找看,但好像找不到啊,“觅心了不可得。”达摩说,好了,搞定,收工,“与汝安心竟。”一切皆空,何来不安?所以心空能生明,所以虚室生白。或者有人说庄子说的是空灵的空(室空了,但室还在),禅宗说的是无的空,在哲学上是完全不同的(研究庄子的特别喜欢从哲学角度论述)。其实不断的无限的空下去,就是无了,今天拆窗,明天卸门,后天揭一片一片的瓦,再接着敲一块一块的砖……最后,室不见了,一切归无,殊途同归。

明白虚室生白的意思,表达上首先应该是宁静的,然后,墨如室的墙,纸如光的白,虚室生白,就应该尽量淡化墨,突出纸。所以,其实什么都不写,只是挂一张白纸,已经是虚室生白的最好表达了。但如果我这样表达,观者会觉得我是一个骗子,就类似西游记里到西天后,孙悟空拿到空白佛经觉得被骗一样,其实空白的才是真经,但既然你看不懂,那就只能退而求次、给有字的了。别误会,我不是说我是如来,观者是猴,我首先也是俗猴而已,所以要俗一点表达。
那么,就不写白字吧,在白字位置留白,但是,这样表达好像还是不够俗。最后,我去请教老子,老子《道德经》里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那么,黑白也相形,把白字处理得越黑,墨越重,就越衬托出墨边的白来,就能把虚白表达得越充分。
所以,首先,让白字小一点,被周围的白包围多点,然后,再考虑把白字的日部,三横全部错叠在一块,变成一个纯黑块,以极黑衬极白。思路有了,还不能动笔,再慢慢捕捉自己的感觉,当有很强烈的动笔感觉时,才铺纸动笔,争取一气呵成,这个作品也确实就一次写成。在落笔的最后,我突然改变主意,把日字中间一横处理成一个重重的黑圆点,觉得这样的黑也够份量。这就像厨师拿捏下盐的份量一样,最后关头忍了忍手,觉得够了。我说这样的过程,并不是在吹这幅小作有多好,它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我强调的重点是创作是需要焖、需要捂的,而这样的焖捂过程,即席挥毫是没时间顾及的。
可能有人说平时不断练字,就是焖、就是捂了啊。不对,平时练习只是培养基本的创作技能,跟具体创作的具体思考是两回事。具体创作的焖和捂要根据具体内容来,譬如我处理虚室生白这个白字,跟处理白日依山尽的白字的思考就肯定会不同。那么,既然已经构思好了虚室生白,不也就可以随时写它了吗?也不行,练习需要重复,但重复是创作的天敌,梵高画了很多向日葵,但从不会复制,郑板桥画了一辈子竹子,也不会重复。创作需要冒险,而不能找一个“安全模式”不断重复,重复只会让作品的生命力越来越微弱。
当然,你可以取笑我是因为水平太烂,所以创作才这么磨蹭。那么,顶级大神是不是不需要任何准备,就可以一挥而就呢?历史上最著名的即席挥毫,应该是这两大作品: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祭侄文稿》甚至还有多处涂改的,但如果你以为这是跟现在的即席挥毫一样,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即席挥毫,有一个更重要的创作前提——情至!他们在写的那一刻是情喷薄而至,不得不发,这才是关键!类似火山爆发一样,不断捂着、压着,能量满了,就爆了!所不同的不过是王羲之的是逸情,颜真卿的是悲情。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传闻王羲之酒醒后再写,也写不出满意的来,原因不在于酒意没了,而是心中那情致已经释放尽了,下次请早。
火山爆发前需要什么?需要焖,需要捂,需要压,需要蓄,这才是艺术创作的过程,从来就没有信手拈来这回事。这就像禅宗的顿悟一样,看着是一瞬间开悟,拈花微笑般的风轻云淡,但为了这一刻都不知道费了多少年苦修,正如郑板桥的诗: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可以把这首诗理解为是说艺术创作的领悟,也可以理解为悟道过程,共同点在于,都很不容易。

而现在,满大街的,不管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野,都有多不胜数的即席挥毫。这样的定时定点的所谓创作,捂从何来?自己整天口口声声吹捧书法是高雅的艺术,偏偏又是这些人正做着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事,讽刺!
启功先生是非常幽默的人,一个和蔼可亲的老顽童,他曾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写得最一般的阶段就是当书协主席的阶段。老先生虽然笑嘻嘻地说的,但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为什么?因为那个时期名气最大,求字最多,下笔前少了累积,甚至是很多时候容不得有思考的时间,不是有捂而发,笔下的字自然就浅了,匠气多了,文味少了。
历史上还有一次值得一说的“即席挥毫”,不是发生在书法界,是在诗词界,就是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看着是走七步就成的诗,但只有天知道这个兄弟相残的痛苦到底折磨了他多久,他才在这刻爆发出这篇旷世巨作。这七步是他爆发的时间,不是他酝酿的时间,兄弟相残这块大石头早早就已经压着他让他喘不过气了!没有这块大石头在胸中焖着、绞着、撕裂着他,就算能七步成诗,也不会流传千古。
我一个不是书法圈的人,为什么多管闲事得罪人呢?因为,这跟审美有关,而审美跟所有人有关,长时间接触没营养的东西,只会让自己的审美触觉不断退化。我对书法圈的事没兴趣,我有兴趣的是你和我的审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