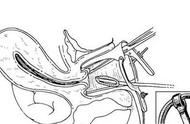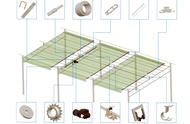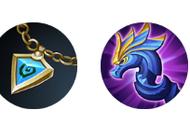曾经反叛逃离主流的年轻人。
今天换成了,拥抱权力,走向体制,渴望医保、福利、公积金。
有这样一群“娜拉”,选择了一种彻底“堕落”的方式出走,挣脱他们不想要的,被规训的生活。
他们当初理想化的愿景,也没有真正实现。
反叛、革命,拒绝保守,与进步,中间并没有等号。
现代世界的图景,年轻人没有过去的方向感。
而如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2021),才似乎能成为当代迷惘者的背书。
女主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
她从未停止过自我觉察与发现,及时修正着自己的选择,渴望自我实现。
她做什么都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拥有各种选择,但到了30岁,仍产生了深刻的徒劳感,对世界迷茫不已。

我们说的坏电影。
“坏”不是指向颠覆、毁灭,而是在这之后的重建、重生。
“坏”,有着蓬勃的暗黑生命力。
但“丧”没有。
丧,不是因为不满,而是因为无望。
人们变得更消沉了。
世界的确在变得更多元也更复杂。
以往被指责“教人学坏”的一部分,如今已是主流,比如那些为女性、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呼号的声音。
《末路狂花》里的女性愤怒,当时看起来是教唆犯罪,现在则湮没于越来越多的女性复仇故事里,成为一种正确。

可于人类整体而言,却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只能接受唯一的正确答案。
J.K. 罗琳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能简单地去承认跨性别者,人们应当警惕这部分人群中潜在的犯罪可能者,若非如此,女性原本的权益可能受到侵害。
这句针对跨性别者的争议言论,使她几乎众叛亲离,以至于《哈利·波特》20周年庆上,灵魂人物罗琳压根没出现。
持不同立场的双方,俨然已势同水火。
当所谓“进步”的主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容任何质疑的霸权,文明,是否已经变了味?
而这,只是当下全球环境的一个缩影。
或许电影里的另一种变化能从某种程度上做出解释。
《雌雄大盗》之后,暴力演变成一种美学。
延伸至现实生活,一种可能性是,罪恶、压迫没有变少,却有了更正当的理由。

于是,文艺作品里,一些张扬的“坏”停留在过往,成为过来人的一声轻叹。
另一些则演变成“正确”和“美”的形式,塑造着人们认知。
以往拍摄过“坏”电影的导演们呢?
有人如伍迪·艾伦,罗曼·波兰斯基,多年后再度踏进当年自己挖出的坑,撞上“取消文化”。
有人功成名就,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与自己曾反对的体系形成合流。
戴锦华老师在《人物》访谈中还提到过“优等生文化”,说得很精彩: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世界范围之内,新一代的导演,多数都是优等生,名校毕业,智商多高多高,但是我就会感觉到这其实是某一种现代主义危机。
……但现在你会看到,好像所有的地方都只有一种优等生的模式和可能性,我会同情这一代人,因为原来我觉得坏孩子有坏孩子的出路,优等生有优等生的前途。但现在看上去,优等生文化的主导位置很难改变,所谓数字化生存,一切是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发生,就使得个性、原创、另类、抗争、抗衡这些东西在大数据本身化为乌有。
我相信这些东西仍然在,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些东西始终是动力。历史的更生,是这些人,而不是平庸之恶创造出来的。
优秀、正确,却也平庸。
优等生意味着,他们是现有体制内的受益者,他们知道如何做才能得到更多。
努力长大,接受主流文化的洗礼和一切多元,做最正确,最有道德的人。
就像有许多文艺作品里一定要集齐各个种族的演员,给主角设定LGBT人设,要让黑人当好人那样简单粗暴。
他们的确也标新立异——在这样一个父权制、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仍广泛存在的时代。
但他们不愿再去真正触碰一个在肤色、种族、性取向、国别之外,政治不正确的,真实的人。
拍摄了《七宗罪》和《搏击俱乐部》的大卫·芬奇导演曾表示,要与常规的电影语言对着干:
“我想用你未必愿意的方式把观众卷入我的电影中,我想嘲弄观众在电影院灯光变暗,20世纪福克斯的标志出现时心中的期望,观众们总在期望什么——我的兴趣就是对它进行嘲弄,这才是真正的必要所在。”
这才是一个“坏”电影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