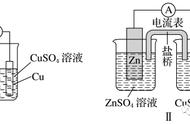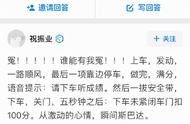最近观看了电影《花木兰》,翻拍自我国《木兰辞》的故事,从精选影评来看,大部分受众十分失望,认为电影拍得“不中不西”,整部片都在诠释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以及美国人对外国文化态度上的傲慢与偏见。
每一种文化在进入他文化的过程中都会变异。他者形象与注视者总是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一方面, 他者形象的建构和表现必须依靠注视者,另一方面, 倘若丧失异国作为他者的存在, 他者形象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者形象虽然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产物, 但他与产生形象的外部现实世界仍有着无法割裂的渊源关系。从中国儒家文化到西方的女权文化, 花木兰形象是被作为文化模块移植的, 移植以后,发生变异是必然的,需要适应移植后所在地域的文化传统、社会思潮和当地人们的心理需求, 才能够被接受。
《花木兰》电影的背景与中国相联系, 但依旧运用美国文化的认知范式;木兰替父从军的初衷——“忠、孝”被“个人英雄主义”等美国式的价值观所替换, 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与实现也代替了儒家传统的“自我牺牲”。这种文化差异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如木兰被安排去相亲时腮红浓艳、额头涂黄、眉毛粗黑,夸张了“对镜贴花黄”的妆容,接着出现的媒人脸上的胭脂涂得也十分浓。而这种外在形象上的丑化在国外影片中也曾出现过,比如美国电影《末代皇帝》中慈禧太后的形象。
片中开始的镜头出现了水稻田地和客家土楼,但《木兰辞》流行于北朝,根据“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的语句,并结合历史上北朝的版图,可以初步推算出花木兰应该是黄河流域的居民,影片中的出现时代和位置并不符台中国历史水稻田地和客家土楼在当时都是不存在的;木兰故事中人物应是北朝晚期的装扮,但在电影中,木兰相亲时的总体妆容服饰都类似于唐朝女子,皇帝等人的造型装扮也与北朝差别很大,是将历史元素错误地杂糅在一起形成的;还有灯笼、太极、凤凰等,都是刻意凸显出的中国元素,呈现出固定化、简单化的刻板印象。《花木兰》的受众定位主要是西方观众,迪士尼深知神秘的东方想象和异域情调在西方是有市场的,因而电影会尽可能地拼凑西方人感兴趣的中国元素。比如影片宫殿场景中丰富的人物形象和明艳的色彩带有欧洲贵族风格,女巫、凤凰等形象安排融入了西方人喜爱的魔幻色彩等。迪士尼有意呈现出这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画面,迎合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从而使影片的传播能够获得最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