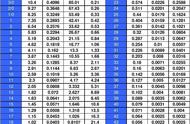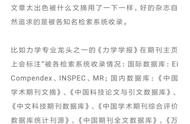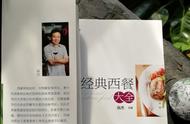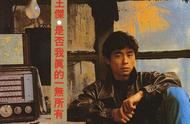明杨有悟:《金刚经》的结尾有这样一句经典佛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字面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的人、事、物、境象..都是空幻的,不存在的,像露水又像闪电,更像泡沫,是生灭无常的,是虚无缥缈了。不论是你执着的,还是不执着的全都是空。
明杨有悟:《遥远的救世主》的作者及她的好朋友都是对国学儒释道研究颇深的人,在故事发展到这个阶段,她想到了《金刚经》里面的这句话,这就是学以致用啊。但是就算是丁元英这样一个有才华非常智慧的人,他也有想尝试祈祷的时候,他在王庙村的时候,辩的牧师都拿他没撤的人。他平常是可以做到“如是观”的,但是在这样的关头,他做不到了。这也是他一直没有涅槃的原因吧,放不下,求不得,想不开,只要有这三个念头存在,就不可能涅槃,从这个维度来看,丁元英属于放不下。芮小丹就涅槃了。

2.沉默与诀别,镇定与悲伤
警察与丁元英的对话部分就不说了,从芮小丹的这个电话在常人的判断里只能有两种解释:1.诀别。这是一个合格刑警的自然做法。2.芮小丹处于职业本能与求生本能的矛盾中,她在这种矛盾的心理驱使下给他打了电话,期望他能给她一个影响她心理倾向的意见。丁元英心里非常清楚,王福田和赵国强作为芮小丹的同事当然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可以通过他的证词排除第二种解释,突出芮小丹作为刑警临危不惧的正面形象。
丁元英更清楚,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会带出一个他对芮小丹的感情问题。如果是第一种解释,人们会质问:以他与芮小丹的感情,既然他知道是诀别为什么不阻止?他怎么可以无动于衷?如果是第二种解释,人们会哀叹:当芮小丹期望他说一句话决定选择的时候,而他却给了她一个高尚而残酷的沉默。虽然有两种解释,但是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判断,都会推导出他对芮小丹面临生命危险却漠然视之的结论。

明杨有悟:其实丁元英并不会在意旁人怎么看待他,只有他自己明白感受到他对芮小丹是放不下的,既然小丹叫她不要打断,那就没必要补充。
如果按第二种解释推导,那么他对芮小丹的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然而,芮小丹作为合格刑警还需要证明吗?“证明”即是对她的不尊重。他对芮小丹的感情还需要别人的理解吗?“需要理解”即是对这种感情的亵渎。丁元英答道:“我只讲事实,不认为。”
明杨有悟: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当下正在放生的一切。而认为是带有主观倾向的。属于个体的所谓道理,其实是事实论据与道理论据的较量,丁元英尊重客观事实,她是否爱芮小丹,他很清楚,不需要别人的认为,而道理论据往往属于我认为应该.....。丁元英是在用行动告诉我们,正面面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就是道。

丁元英伸过手去,轻轻抚摸着芮小丹的相片上的脸庞和长发,心里喃喃自语道:“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来去自如。丫头,不简单哪。”他像平常一样打开音响,芮小丹最爱听的那支《天国的女儿》旋律充满了整个空间,在音乐声中,他在客厅里缓缓地踱步,踱了一会儿又坐到沙发上,开始慢条斯理地整理工夫茶具。他将茶杯、闻香杯、公道杯、盖碗一一用茶巾仔细地擦拭,那种专注神情似乎是在做着一件极精细的工作。
明杨有悟:丁元英悟了,他悟到了芮小丹的超脱,他想故作镇定,但是内心深处却在酝酿一场悲伤的情绪。这就是佛家说的安住,当悲伤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阻止它,我们可以自观,或者叫内观,悲伤要来便来,最后肯定会走的。当我们的任何情绪要来的时候我们都不愿跟随它,但是也不要刻意阻止情绪、感受的到来。
然而,无论他怎么对抗、舒缓、掩饰,都无济于心头的疼,那是一种心如刀绞、无可忍受、无可遏抑的——疼。他以为他是明白人,他以为他可以从容、达观,但是当他静静地泡好一杯茶静静地喝到嘴里的时候,这杯茶却被喉咙的一团东西堵住了,也就是在他试图咽下这杯茶的一瞬间,一股生理无法控制的东西突然从胸腔喷出,他本能地紧闭上嘴,快步走到卫生间的洗手池,吐出的是一口鲜红鲜红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