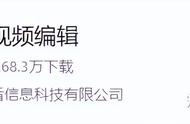近日,上海文史专家顾景炎生前所藏明代李流芳等六人《重修九品观弥陀殿等募缘疏合卷》在2019年朵云轩艺术品春拍上以高价落槌,引发社会多方关注。这件传世合卷上的文章皆为募修当时的嘉定南翔白鹤寺建筑而撰,作者除李流芳外,还有嘉定徐兆曦(礼部尚书徐学谟之子)、张鸿磐、徐时勉、云间朱国盛、平湖倪长圩,均为晚明时期的江南士人,其中以李流芳声名最盛。
李流芳(1575—1629),字茂宰,一字长蘅,号檀园,又号香海、泡庵、六浮道人,晚号慎娱居士,明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南翔镇(今属上海)人。他善诗文,工书画,精通印刻,有《檀园集》十二卷及若干书画、印刻作品传世,其课徒山水画稿收入清代李渔所编《芥子园画传》。

李流芳画像
其实,作为一位文士,李流芳曾多次以撰作疏、序、缘起等文章的方式为故乡嘉定以及苏州、杭州等地的佛教寺庙化募善款,助力于江南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今朵云轩所拍《重修九品观弥陀殿缘起》仅是其中一例而已。

顾景炎藏明代李流芳等六人《重修九品观弥陀殿等募缘疏合卷》(局部)
声价、身份与交游:众僧求请李流芳劝募之因由
李流芳之所以多为僧侣所请,撰文以勖捐募,主要是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李流芳诗文书画印刻皆工,当世即负盛名,因此具备较强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明天启、崇祯间,四明人谢三宾任嘉定知县,对乡邦文献整理颇为关切,《檀园集》就是在李流芳去世后,由他支持出版刊行的。他在《檀园集序》中说:“长蘅累世簪缨,科名廿载,文章书画,绚烂海内。其徒盗窃名姓及模勒炫售者,犹足以奉父母、活妻子。……长蘅之所流传,未知鸡林等国何如。凡我公卿学士,下至贾竖野老,以及道人剑客,无不知敬慕若古人然。”李流芳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同时期的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对流芳的评价更高,认为“其人千古,其技千古”,“其交道亦是千古可传”(《容台集》别集卷四)。
实际上,明清两代的嘉定文化尤以明万历以后的晚明时期与清乾嘉之世最称隆盛。乾嘉时期的嘉定文化人物以乾嘉学派的钱大昕、王鸣盛为标杆。晚明时期,则以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为代表,世称“嘉定四先生”,四先生当中,又以李流芳为翘楚,在文坛艺苑皆享有清誉。盛名之下,李流芳凭借个人魅力感召、发动募捐的优势也就毋庸置疑了。

“嘉定四先生”雅集碑拓(原碑现藏上海嘉定孔庙)
其次,作为佛教居士,李流芳笃信净土,发心护佛,其意拳拳。据《光绪嘉定县志》卷三十,嘉定东林庵为李流芳早年读书习文的场所之一,其自小受释氏耳濡目染必不在少。万历间,他皈依净土宗第八祖、“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袾宏(俗姓沈,名袾宏,字佛慧,晚居杭州云栖寺,因以为号,别号莲池),“其法名广(山扈)”,“自署云栖弟子,殆皈依莲池大师者”(叶恭绰《矩园余墨序跋二•李檀园手写四十二章经跋》)。流芳《抱疴真歇禅师塔院夜坐偶占》诗下有注:“禅师偈云:‘老僧自有安闲法,八苦交煎总不妨。’”这里的禅师即指云栖袾宏。他的另一诗作《皋亭送张尔完东归,尔完从慧法师听讲弥陁疏钞,初受五戒》所提及的“慧法师”指的也是云栖大师。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十二岁的李流芳与其好友晚明文坛领袖钱谦益偕举于南京。此后,他先后八次北上京师赶赴会试,一无所获,最终于天启二年(1622)绝意仕进。放弃举业后,李流芳奉母念佛,晚岁尤致于此。对此,钱谦益如是说:“(流芳)再上公车不第,又再自免归,皆赋诗以见志。自是绝意进取,誓毕其余年暇日以读书养母,谓人世不可把玩,将刳心息影,精研其所学于云栖者,以求正定之法。未久而病作,犹焚香洮頮,手书华严不辍。”(《李长蘅墓志铭》)比流芳稍晚的嘉定名士侯峒曾亦云:“(流芳)惟西竺氏,久闯其藩。恨不精猛,遂彻根源。短景既促,皈依弥敦。钟梵之音,爰及旦昏。”可见,除文学、艺术创作以外,佛教也是晚年李流芳极为重要的精神依归,所谓“精舍繙经招净侣,晴窗斗墨趁闲身”(钱谦益《客涂有怀吴中故人六首•李先辈长蘅》),正是其佛系游艺生活的生动写照。李流芳尊奉释氏、研修佛法若此,他为僧侣所请,助力佛教慈善事业当自在理中。
再者,李流芳喜交朋辈,对待朋友慷慨大方,通达平易,乐善好施,自然也乐意动员更多的人参与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作为挚友,钱谦益对李流芳与人交往的原则、态度、方式均十分了解,他说:“(流芳)与人交,落落穆穆,不以握手出肺肝为信。磨切过失,周旋患难,倾身沥肾,一无所鲠避。……家贫,资修脯以养母。稍赢,则分穷交寒士,卒未尝立崖岸之行,以洁廉自表襮也。……为人和乐易直,外通而中介,少怪而寡可。”(《李长蘅墓志铭》)对此,谢三宾也有类似的表述:“(流芳)为人慷慨,遇不平事,无问朝野,辄义形于色。然慈惠乐易,其素性也。喜接后辈、周贫交,尤喜成人之美,未尝有所怨忌。”(《檀园集序》)
中岁以来,李流芳多在嘉定、苏州、杭州,特别是西湖一带游历流连,“中岁于西湖尤数”(钱谦益《李长蘅墓志铭》)。他认为“天下佳山水,可居可游可以饮食寝兴其中而朝夕不厌者,无过西湖矣”,因此“二十年来,无岁不至湖上,或一岁再至,朝花夕月,烟林雨嶂,徘徊吟赏,餍足而后归”(李流芳《题画为徐田仲》)。在西湖等地,他结交的朋辈甚多,其中就包括不少高僧名隐、缁流黄冠。李流芳“所至诗酒填咽,笔墨错互,挥洒献酬,无不满意。山僧榜人,皆相与款曲软语,间持绢素请乞,忻然应之”(钱谦益《李长蘅墓志铭》)。他还在各处佛教胜迹题字作画,杭州“法相寺壁有画竹,莲居庵有书经石刻”(《明李流芳西湖卧游图题跋》卷末),南翔白鹤寺亦如此,“壁间旧有擘窠大字数行,为长蘅先生笔”(《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九),留下一段段士僧交游的佳话。正是以诗文书画为媒,李流芳与许多僧侣建立了良好的情谊。《檀园集》就有多首与高僧上人往还唱酬的诗歌,如《登铜井访三乘上人》、《赠别不了上人》、《灵隐次颖法师韵》等等。流芳与侒沙弥之间的深挚友谊更是令人称道。侒沙弥俗姓胡,曾跟随流芳二十余年,伴其走南闯北,后不幸患病,死前十日皈依佛门,受沙弥十戒。沙弥生前酷爱流芳之画,收藏颇多,离世后,流芳十分悲伤,不愿意将其藏画送人。虽然最终拗不过友人张伯英的央求,还是将沙弥所藏相授,但他却一再嘱咐张氏:“子其无忘沙弥之意哉?”因为在流芳看来,不仅收藏者的名字将“附书画以不朽”,自己的画也“将借好者之癖以不朽矣”(参详李流芳《题画册(二则)》)。有了朋辈情谊作为铺垫,僧侣们向乐结善缘的李流芳求文化募便更成为理所当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