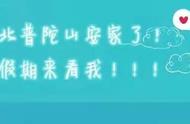作者:徐晋如
欧阳修幼年丧父,由其母郑氏鞠育长大。郑氏曾对他讲过他父亲欧阳观为官时,常常半夜还详审官书,每见死刑犯无法减刑,就废书长叹,感慨说:“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欧阳修闻此语,服膺终身。故刘熙载《文概》评他的《新五代史》诸论,以为“深得畏天悯人之旨”,其他文章“亦多恻隐之意”。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是千古为人传诵的一篇名文。此文短小精悍,先扬后抑,借批判唐庄宗之失国,而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大道理。他是以情主文,开端即是一通情见乎辞的感慨:“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再娓娓叙写庄宗得国的过程,文笔简古:“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接写庄宗失国,更不烦枝蔓:“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何其衰也”照应着前文的“可谓壮哉”,这样叙事中洋溢着充沛的感情,这是欧文的一大特色。刘熙载说他“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人之指趣为多”(《艺概·文概》),则其文一是简洁,二是富于感情。有感情,自能以情主文,以气行文,而不劳经营,无蕲于法度了。
此文末段,欧阳修感慨说:“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这段文字仍是带感情的议论,不只以思想之深刻猛锐见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段话虽是古文,但仍寓以骈体之法。“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与“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在意思上是对偶的,但形式上却是散体,“方其盛也”与“及其衰也”所引出的句子亦然。而“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及“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本就是对仗精工的骈语。《文心雕龙·丽辞》云:“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凡名言隽语,多宜骈偶,这不是刻意去经营的结果,而是文气自然流行所致。(徐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