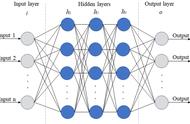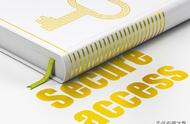明中后期以来,作为“士大夫之一艺”的印章进入文人的视野,成为文人的艺术活动,并得到文人的重视,印人也因此提升了自身的地位。而此前,印人身为工匠地位低微,为文人所“不齿”。“工人印”与“文人印”的分野也逐渐形成。
本文摘编自朱天曙所著《明清印学论丛》一书的《明末清初印人身份变迁及其背景初论》一文。文章探讨了“印人”这一特殊身份在明末清初的变迁及其形成的社会背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诠释了印人身份的出现。
本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取,内文有删节,文章由出版社授权转载。

《明清印学论丛》,朱天曙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原作者丨朱天曙
摘编丨董牧孜
明代以前,“印人”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
明末清初著名鉴藏家周亮工
(1612─1672)
撰成《删定诗人传》、《读画录》,并撰成历史上第一部记录印人的重要文献——《印人传》,把印人和诗人、画家一样予以关注。

周亮工所撰《印人传》。
《印人传》的写作昭示了“印人”作为一种特殊身份进入文人的视野,有别于一般的“工匠”。宋代以前,有以篆书书法名世者,如唐代李阳冰
(约721─785)
以小篆名世,他的小篆圆润盘曲,中唐篆书大盛,他有复兴之功。同期善篆者还有如瞿令问、史惟则以悬针篆名世,富于装饰性;袁滋
(749─818)
在小篆中参以古籀,多有新意。五代、宋代时,写篆书著名者如徐铉
(916─991)
、徐锴
(920─974)
、郭忠恕、薛尚功等人。但这些人都以篆书影响当时,而没有专门以印名世者。
到了元代,赵孟頫、吾丘衍等人开始自己在印章上写篆书,印章从实用功能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专门的艺术。到了明代中后期特别是万历以后,印章发展更加迅速,印人身份也越来越得到文人的认可,文人也不断参与到印章的艺术实践中,印人和文人的身份也不断处于游离的状态中。
在以文人为主导趣味的苏州和南京的文化环境中,印人的文化品味不断提高,印人和文人的来往密切,印材变革和功能变化也使得印章的“文人品味”成为可能。
工匠的兴起:
印人身份是如何提升的?
“印人”最初是以工匠身份出现的,如先秦时期的铜、陶玺印由铜工、陶工完成,秦代的官印制作有符玺令、丞和符玺郎进行管理,由印工来完成。
到了明代,印人是如何把“工匠化”的技术赋予文人品味,而使印章成为文人书斋、案头的清玩?这种转变与明代文化环境有何关联?如何具体呈现“印人”身份的这种变化?我们先来探寻中国古代关于工匠的记载。
《礼记》中说:“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这反映了上古时期“执技”的工匠不能改行,也不能与文人士大夫交流。国家设立“工官”、“工师”、“巧工司马”等来对工匠进行管理。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中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录。唐代诗人韩愈《师说》中也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这些都反映了工匠地位的低微,为文人所“不齿”。
尽管如此,文人士大夫仍然需要与工匠“合作”或从工匠的实践中获得启示。汉代的官印,有符玺御史、印曹、尚符玺郎等职官专门管理符玺和印章刻制,由兰台令史篆写印文后,交由印曹的工匠刻制。如史学家班固善篆书,并曾以此职监造官印,和工匠进行“合作”。唐代朝野对石刻刊镌十分重视,名家书迹多请名匠刊石,皇帝甚至指定专门名匠刻石,如开元十年
(722)
,唐玄宗亲自撰写的《西岳太华山碑序》就指定名匠吕向为镌勒使刻于西岳。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亦有不少关于工匠的记载,这些内容虽然零星,但已表明:工匠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其社会功用是不能忽视的。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
明代中期以来,随着江南一带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市民文化与审美意识的滋长,苏州一带的木版年画、南戏、小说、书画、园林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与其相关的印工、装裱工、雕刻工等“工匠”兴起。同时,思想界个性解放思潮的出现,晚明的文化环境也发生变化,文人也更加的关心各类工匠以及他们的工艺品。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所谓“古玩”即是装点生活和雅玩的工艺品。这些物品进入士大夫的生活,他们的艺术价值在文人的雅集、把玩、娱乐中得到挖掘,并不断被记录下来,进而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直至被抬到与诗文书画相并列的地步。
袁宏道在谈“时尚”时称:“古今好尚不同,今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杨茂、彭君宝,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张岱《陶庵梦忆》还记录濮仲谦的竹雕成为“抢手货”,“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而新安墨工方于鲁还与汪道昆结成姻亲,更是“奖饰稍过,名振宇内”,这些昔日为文人所不齿的“梓匠轮舆”之人这时不断与文人交流,社会地位大大提升。
徐巨源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晚明文化风气时,他把制陶、制墨、攻玉、刻印的工匠和文人艺术家放在了一起讨论,表彰他们的突出成就,反映了文人艺术家和工匠的分野已不再明显。
“工人印”vs“文人印”:
印人的“鄙视链”
事实上,晚明士人与工匠之间的互动十分频繁,士人也有了强烈的“通俗”意识,他们身份的界限也变得不太明显。如张岱以绘画上的事例来讨论印章一样,印章上文人与工匠之间的合作从明代中期文徵明
(1470─1559)
、文彭
(1497─1573)
父子开始赋予了印章艺术新的内涵,并将这门艺术提升到新的高度。
文徵明是中国文化在明中期独立成形发展中的代表人物,他通过书画作品的创作、赏玩、赠友、交换等活动,建立了特有的“文派”典范,从而塑造了文人特有的生活风格,有别于一般的平民,他在绘画上即有相类的与工匠合作的作品。
台湾学者石守谦先生曾以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寒林钟馗》作品为例作深入研究,指出此图的寒林背景确为文氏手笔,但主角人物的钟馗有着讲究的姿势、细致的表情,显示出画者对人物画技巧的高超掌握,决非文徵明所为,其作者应为与文氏素有交往的职业画师仇英。图中钟馗特有的文雅,又与仇英一般所作不同,显示了文氏在背后的指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