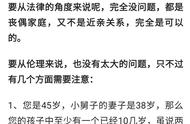可能改变家牛驯化史的中国东北牛下颌骨,牙齿有严重磨损(可能叼嚼子导致的),
图源:Zhang, et al., 2013,Nature Communications
而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华大地上,驯化的沼泽水牛在水稻田中和智人一同踏上征途,这些在热带和亚热带气候下生存的水牛还挺怕冷,因此未能像家牛一样走向北方的草原。不过南方大片的水田和温润潮湿的气候满足了它们的生存,这类耐粗饲且抗病力强的巨兽还拥有着惊人的力量--虽说家养的沼泽水牛体型也不和家牛差多少,但是力量不比家牛差,沼泽水牛的牵引力是家牛的1.5到2倍。

野生沼泽水牛,
图源:Sandesh Kadur / NPL / mindenpictures
科学家们曾经对沼泽水牛和家牛的基因组进行过比对,发现家牛的AMD1基因只有一个拷贝而沼泽水牛有三个,AMD1编码了多胺合成代谢中的关键酶而多胺也在肌肉生长中至关重要。或许是较多的AMD1拷贝数给予了水牛强大的力量吧。这些同水稻相伴相生的家养沼泽水牛,在拥有强大力量的同时,也因为人为的选择变为温顺的巨人,它们的OXTR基因与野水牛有所不同--OXTR基因在人类基因组内是调节人社会认知与行为的关键基因,在水牛的基因组内可能就影响了水牛在田中劳作时如何响应人的命令。
而它们在驯化的过程中也对淀粉的消化能力更强--毕竟会吃含淀粉的米糊,这是数千年来食谱的更改。这些人类的工作伙伴为农耕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笔者拍摄于云龙县检槽乡的家水牛,体型比起野生亲戚小的多,图中水牛一雄一雌

笔者拍摄于云龙县检槽乡的家水牛,雌性
自从同人类搭上了一条船之后,牛也顺着人类文明的交流进行了相关的扩散。尤其是家牛,从印度和中东走到了埃及和欧洲,还有中国,此外非洲草原上的黑人们很快也是放牧着大群的家牛。在新航路开辟之后,家牛又来到了新大陆和大洋洲,缔造出了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巴西的美味烤牛肉。
在近几百年里,迈入工业化时代的人们也开始了规模养殖和育种改良--想要吃精肉有比利时蓝牛,想喝牛奶的话荷斯坦奶牛(黑白花奶牛)那足有自己体重十倍的年产奶量足够让人直呼真牛,还有奶可喝肉可食更可以拿来耕地用的西门塔尔牛。而西门塔尔牛,在云龙县可谓是深受养殖户的青睐,毕竟什么都能干,养了自然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