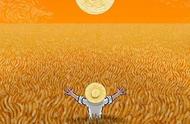蔡亮著,付强译:《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在中国历史上,西汉的巫蛊之祸大概是最为著名的巫术事件。有关巫蛊之祸,既往的相关研究虽多有涉及(如近来引起很多讨论的辛德勇先生《制造汉武帝》一书对巫蛊之祸有专章讨论,三联书店2018年版),但却少有专题研究。当然,本书的主旨并非聚焦巫蛊之祸的史实,做史学式的考证研究,而是着眼于更为宏大的主题,即在巫蛊之祸所引发的历史余波中,儒生如何作为一个团体力量逐渐崛起,并确立了后来数世纪儒生帝国的政治基调。作者强调:“巫蛊之祸不仅仅是一场牵涉皇室的政治阴谋,也是使中国成为一个儒家帝国的历史转折点。”作者认为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所确立的儒生可以凭五经学养而参与政治的说法有一定的虚构性,司马迁的叙述与其说是在记述史实,毋宁说是在建构历史,背后暗含的是对当时现实世界的批评立场。通过更为细致地分析,作者提示我们,“在公元前91年至公元前87年,出身相对贫寒的儒生们通过他们敏锐的政治判断与优秀的行政管理能力,准确地利用了巫蛊之祸形成的权力真空逐渐获得了政治权力。为了给他们的政治成功寻找合理依据,儒生们回溯历史,重构了一个武帝治下欣欣向荣的儒林。”(第5页)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提到的那样,书中一些观点的“冲击力”在出版过程中就遭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本书所触及到的史实与阐释或是后来相关研究所绕不开的学术话题。
5.游子安、志贺市子《道妙鸾通:扶乩与香港社会》

[日]志贺市子著,宋军译,志贺市子译校:《香港道教与扶乩信仰:历史与认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本书研究香港社会中的扶乩活动,论述范围极广,自历史中香港坛堂之源流,到十九世纪末的扶鸾救劫运动,以至二十世纪扶乩团体的尊孔思潮等;从扶乩人物与香港的文化氛围、扶乩与香港潮州社会的关系,到乩坛与行善救济等,将扶乩纳入到香港的历史、社会、文化脉络之中来做深入之考察。两位作者对香港的宗教文化素有研究,志贺市子有关于香港社会中扶乩活动研究的专著出版([日]志贺市子著,宋军译,志贺市子译校:《香港道教与扶乩信仰:历史与认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加上作者与乩坛及乩手的直接交往与考察,使得此书既具有思想、宗教研究的厚重维度,又有着人类学的在场经验,是地方宗教研究中的佳作。
6.颜芳姿《妖怪、变婆与婚姻:中国西南的巫术指控》

颜芳姿著:《妖怪、变婆与婚姻:中国西南的巫术指控》,台北:三民书局,2021年
本书是作者基于在贵州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撰写而成。当地流传着著名的“变婆”妖怪故事,变婆活着时与常人无异,但死后却会变成令人恐惧的神秘力量。据说变婆死后三天就会变成猫,或以美妇形象出现,又或异变成兽,危害人间。变婆只是乡野之怪谈,还是真实存在的怪物?变婆如何影响当地人的婚姻观念?变婆传说背后包含着什么样的秘密?作者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希望通过变婆现象及其中包含的巫术指控,来思考边缘地区汉族与非汉民族间的关系问题。如作者所言,“巫术跟医学一样,都在帮助人们重拾生命的力量,拿回主导权,设法干预命运,协商社会关系,对社会和个人所面临的灾难不幸和困惑不安提出有意义的解释,对社会危机提供风险管理的因应策略。”(序言)
7.杨伯达《中国史前玉巫教探秘》

杨伯达著:《中国史前玉巫教探秘》,北京:故宫出版社,2020年
杨伯达先生常年从事玉文化研究,尤其重视巫玉文化的结合,此前曾出版《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巫玉之光》(续集)(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中国史前玉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等专著,本书亦是从巫术与玉文化关系的角度所撰写的全新力作。作者将早期原始宗教称作“巫教”,因早期许多地区的巫术强调“以玉事神”,作者就进一步将“巫教”定名为“玉巫教”。“巫教”与“玉巫教”的命名或有争议之处(如饶宗颐先生在《历史学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巫”的新认识》中所进行的讨论,见《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成立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2年),但强调玉器与巫文化的关系,则是十分必要的。本书将“玉巫教”分为早、中、晚三期,按照地域分为夷、越、蛮三大族群,又将玉神器分为信仰崇拜类(如龟、猪、鸮、鹰、云、风、海、鱼、龙、凤、蝉、蚕、树、稻、慈姑等)、美身类(如玉镯、玉璜、玉环、玉梳背等)和供神食飨三类。本书所涉及的考古资料极为丰富,作者的论述视野宏阔而又具体而微,对学界理解早期巫玉文化当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8.张保同、王军青《巫术文化视域下的汉画像和原始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