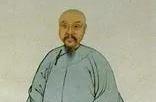大鲵潜在的遗传单元(引自Yan等,2018)
根据大鲵属物种分布区域特点来看,野生大鲵的栖息地多位于河溪的上游,一般分布于盆地边缘的山区,两岸山体较高,并具有较多的深洞暗流。其栖息地周围植被覆盖度都较高,河面窄、水深较低、河床砂石多,河水常年清澈,水质矿化高,水温的变化范围在5℃-25℃。大鲵生存的环境湿度高于80%,因为高湿度的环境条件有利于大鲵的生长发育。
就水体环境来看,该物种喜欢水体流速较缓、清洁、食物资源丰富(主要为溪蟹、鱼虾等)且溶解氧含量较高的水体环境,对水体酸碱度比较敏感。其栖息地水体的酸碱度在6.50-8.63之间,总硬度在120-174毫克/升之间。
就种群密度来看,1978-1999年间,各分布区中大鲵的种群密度基本都大于每千米50尾。但在2000-2019年间,大鲵野外种群的密度持续下降,现在大部分有大鲵分布的保护区内其种群密度都在每千米1尾以下,仅有少数保护区内的大鲵具有较高的种群密度(如河南商城、浙江开化、广东连南、广东河源等地)。
就栖息地状况来看,1978-1999年间,大鲵的栖息地破坏并不太严重,个别的水电设施建设和较轻微的水体污染可能对其生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在2000-2019年间,随着大鲵栖息地内水电设施建设的快速增加,造成了其栖息地破碎化,阻断了其迁移通道。同时,随着水体污染的加剧(如挖沙、生活垃圾及污水排放、农药及化肥残留等),部分栖息地水体环境已不再适合大鲵的生存和繁殖。
从大鲵的种群动态趋势来看,1978-1999年间,由于市场需求的增加,大鲵收购价格升高,导致大鲵种群资源急剧下降。在2000-2019年间,我国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并对大鲵进行了相关立法保护,大力杜绝偷猎盗捕事件的发生。同时,随着大鲵资源的持续下降和大鲵人工繁殖技术的成熟,野外放流开始作为大鲵野外种群快速恢复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2010年以后,大鲵的野外放流规模不断扩大。虽然野外放流对大鲵野外种群的恢复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整体成效并不明显,仅在个别保护区中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放流种群。
大鲵保护成效仍待加强

1978-1999年间,我国对大鲵的保护行动有限,尽管设立了24个大鲵自然保护区,但对大量存在的盗猎盗捕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对大鲵保护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大鲵保护成效较低,大鲵种群数量下降明显。2000-2019年间,随着执法力度和对大鲵保护宣传力度的加大,以及大鲵自然保护区的进一步增加(23个,其中含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再加上大鲵栖息地保护和增殖放流活动的开展,我国对大鲵的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某些保护区中的大鲵种群有所恢复。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成效并不明显,还需继续推进相关保护工作。
具体来说,截至2015年,我国已经建立以大鲵为主要保护对象或与大鲵相关的自然保护区47个,这些保护区大多分布在大鲵的原产区。同时,我国也建立了一些非原生地大鲵保护区,作为迁地种群保护的种质资源储存库。但对比大鲵当前分布点和47个保护区相对位置时,当前的大鲵分布区仅有约21%在保护区内,表明大鲵还存在相当大的保护空缺。

大鲵在我国放流概况。(A)2002年以来放流大鲵个体在我国的变动趋势;(B)全国不同省份的大鲵放流个体数;(C)大鲵在我国的放流点和放流方式(仿于Shu et al., 2020)
增殖放流也是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方法。自2002年以来,我国为了恢复和保护大鲵种群数量,各地区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大鲵人工增殖放流。目前,中国大鲵放流数量累计超过27万尾,放流的省(区、市)共有16个,包括安徽、福建、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陕西、四川、云南、浙江、重庆和北京。其中陕西省放流数量最多,北京市放流数量最少。放流数量的趋势呈先增后减,2016年放流最多,高达6万尾。但就保护效果来看,大部分保护区的保护成效并不明显,增殖放流的成活率也较低。全国仅在部分保护区内发现了较大规模的大鲵种群,主要有河南商城、浙江开化、广东连南和广东河源等地。个别保护区内还存在过度旅游开发(漂流等项目),严重影响大鲵的生存环境。同时,由于不清楚放归个体的遗传背景,出现了部分保护区的放归个体不是来源于当地遗传支系的情况。这不仅给当地种群带来了遗传污染,还可能因压倒性数量优势与当地种群出现竞争,从而加剧原生小种群灭绝的风险。
大鲵未来研究和保护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