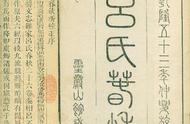河蚬喜欢生活在沙滩临水的边缘,在湿漉漉的洁净的沙面上,会出现一个个大小深浅不一的小洞,那就是河蚬的家。我们只需弯下腰去,用手指一抠,一只手指头大小的河蚬就被挖了出来。

落在掌中的河蚬,其实就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圆底三角形的贝壳,在阳光下微显光泽,黄灿灿的,十分的洁雅素净。
河蚬对水质的要求非常严格,在稍有污染的水域都难以生存。即使在洁净的水域里,贝壳的颜色也全因沙泥的比例不同而发生变化。在纯洁干净的沙子里,河蚬的颜色是棕黄色的,如果沙子里杂有泥土,颜色就变成了黄绿色,而在淤泥为主的环境中,颜色就变成了黑褐色。它们有点像陆地上的变色龙,调整着自己贝壳的组成元素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纯净的棕黄色固然赏心悦目,可我们的注意力并不会放在颜色上,我们更在乎的,是河蚬个头的大小。当我们挖出一只比拇指还大的“河蚬王”时,会高兴得不得了,这时,稍小一点的都看不上眼了,总想着再找一个,再挖出一个更大的来。

河蚬除了在潮湿的沙堆里安家外,还会爬到沙滩边缘的浅水区寻找食物。当时,我们也不懂河蚬以何种东西为食,就天真地认为它们就靠吃泥沙为生。
挖完了沙面上的河蚬后,我们便会把注意力放在浅水的沙底,我们必须弯下腰,贴近水面,才能看清河蚬是趴在沙面上还是躲在沙洞里。好在江水十分干净,清粼粼的明澈如镜,清澈见底,连水中细小的晶莹剔透的砂粒都清晰可辨,那一个个指头大小的河蚬当然也就无所遁形了。或挖或捡,不一会就可以弄上几十个来。

捡完河蚬,我们还会意犹未尽地泡在清凉的河水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这才踌躇满志地拖着沉甸甸的装满河蚬的小桶回家去。
大人告诉我们,刚捡回来的河蚬肚子里含有沙粒,所以要放进一个大盆,用清水静养两三天。
在等待美食期间,我们也会充满兴趣地静坐在大盆旁边,观察河蚬的活动。刚开始,河蚬都是紧闭着贝壳,沉在水中,慢慢地,可能是感觉到没有什么威胁了,才缓缓张开两扇贝壳,伸出小吸管轻轻晃动,如同侦察敌情的雷达一般,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迅速合上贝壳,沉入水底。我们经常会找一根细小的棍子,慢慢地靠近,突然插进河蚬的两扇贝壳之中,受惊的河蚬会马上紧闭起来,把小棍子紧紧地夹住,力道十足,我们可以提着小棍子把河蚬吊在半空中。

这种情形很容易使人想起“鹬蚌相争”的成语故事。本来,在所有的贝类中,河蚬的体型应该是最小的,才拇指头大,尚且有如此强大的咬合力,所以一只大河蚌能把鹬鸟的尖嘴夹住,也就不足为奇了。
河蚬虽小,却有多种吃法。我们家通常是用来清炒和煮粥。
清炒河蚬很简单,特别是使用的佐料简单,除了油盐料酒外,最多也就是加上少许的紫苏和葱姜。而偏偏只有这种简单的做法,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食材的鲜味、原汁原味,自然之味。这恐怕也是为河蚬量身定做的方法,因为河蚬个小,肉少,重点自然就不能放在量上,而必须在味道上下功夫,就像现代人爱吃小龙虾一样。况且,和小龙虾相比,河蚬还多了一份素面朝天的鲜美。
河蚬煮粥,同样有那种自然清淡的鲜美。那个年代,我们根本不懂海鲜为何物,能吃上几条咸鱼干已经很不错了,偶尔吃上一次淡菜或墨鱼粥,比过年还兴奋。河蚬粥,就成了我们的“海鲜粥”。
对河蚬美味的追求,成了我们经常去寻挖河蚬的动力。对我们而言,那是一片神奇的沙滩,明明我们已经反复寻挖,似乎已经把沙滩上和浅水里的河蚬挖得一干二净了,可几天后上去一看,沙滩上又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小洞,随手一挖,又是一只黄灿灿的大河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