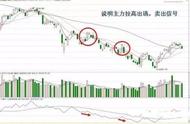从这一点上,大黄蜂最终选择科迈罗在时间点上并没有什么硬伤,而且大黄蜂如果需要变身必然也会选择美国汽车,日本汽车虽然成为70年代美国之后的主流,但日本汽车在美国通常被认为没有性格,因此在美国畅销的福特野马、F150,乃至美国之宝科尔维特成为最具美国范儿的车型。
这样强调个性的国度,甲壳虫这种国民家用车又是如何进入美国的呢?这一切都源自那个被称为广告界经典案例的“往小了想”(Think Small)广告。

这则广告最开始是一家小广告公司DDB为了节省成本而印刷的,在当时许多汽车广告都采用浓墨重彩渲染的车身形象,甲壳虫一反常态,采用了成本更低的黑白印刷。通过只占用版面二十分一,甚至连车都看不清的车身形象,和当时追求大和强的美国汽车形成了强大反差,让美国人看到黑白时就想到了经济,而且甲壳虫在加油、停车时巨大的便利性让甲壳虫一炮走红。
这个广告让年轻人首先关注到了这款车,恰好碰到了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主导的社会,人们都有“无论身体和思想,至少有一个在路上”这样的执念,所以年轻人对车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正如《大黄蜂》里的女主角一样,拥有一辆车并不是那么简单。

拥有一辆车的确不简单,但拥有一辆甲壳虫特别简单。简单到,只要年轻人愿意在暑期里稍微勤奋一点就可以买一辆。终于在1967年,十多万人涌入了旧金山-阿什伯里区,形成了被后世传诵的“爱之夏”。(《大黄蜂》里,甲壳虫也有在金门大桥附近的场景)。
在那个夏天,摇滚开始慢慢滋生,众多年轻人开始进入一种崇尚自由、乐于分享、叛逆但创意乃至革命近乎疯狂的状态,一切有形的都要打碎成为无形的,在那里你可以穿着你喜欢的奇装异服,自由地表达你的创造力,自由地跳舞,自由(免费)地表演音乐,以及不需要房租的房子。

可以说,我们如今在享受的现代音乐节文化,追根溯源都可以来到这里。
Scott McKenzie的《SanFrancisco》就演唱了当时的状态,男女都披散着头发、头上别着鲜花(60年代的美国嬉皮运动中,花卉作为爱与和平的象征,他们反对美国参与越战)、赤脚游荡在街头、躺在金门公园的草地上聊天,街道或是陌生人家的地步就是他们的住所,道路上到处都要摇滚歌手在歌唱,嘴里叼着大麻,搂着自己的女朋友,依靠在一辆辆甲壳虫上。
为了表达叛逆,大多数甲壳虫并不像《大黄蜂》里那么素,而是被年轻人喷上了各种各样的多彩图案,这也是为什么甲壳虫在美国影响力如此之大的原因,同样备受年轻人喜欢的还是大众MicroBus,他们正确的出现的样子应该是下面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