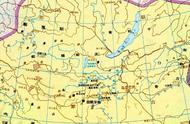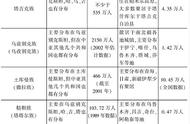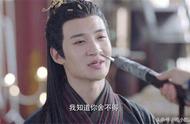从词源学角度看,ujʁur一词由动词词根uj-(凝结、凝固、团结、联合、统一、聚集、汇聚)附加后缀-ʁur构成。如《突厥语大词典》中便收有ujdï(uj-的第三人称过去时)、ujuldï(uj-的被动态形式,第三人称过去时)、ujturdï(uj-的使动态形式,第三人称过去时)、ujuʃdï(uj-的集合态或称共同态形式,第三人称过去时)等词。-ʁur为附加于非及物动词词根后的使动态附加成分。受语音和谐律影响,又有-gyr/-gær/-ʁar等变体形式。在语音顺同化规律的作用下,有时其前面的辅音脱落,故而又有-ur/-yr/-ar等简略形式。-ʁur及其变体附加于非及物动词词根后,可使原动词变为及物动词。附加-ʁur及其变体形式的词干,可连缀其他附加成分或人称词尾;也可直接使用,表示祈使、号召、命令、愿望等意义。波斯史家拉施特(1247~1318年)在《史集》中将ujʁur的语义释为“他和我们合并,并协助我们”。中亚史家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在《突厥世系》中称,ujʁur的意思是“聚合在一起的人”(yapouschghour,=japïʃʁur),即“使依附”或“使粘住”。据此可知,该词最初的意思为带有祈使、命令、号召、愿望等语气的“联合”、“团结”、“统一”、“聚集”、“汇聚”,可译为“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统一起来”或“聚集起来”。其名词意义则是作为固定专名使用后才具有的。

曾有研究者认为,ujʁur一词原本就是民族名。还有人称“此字被用作民族称谓,至少已有千余年历史,甚至超过二千年”。如此一来,也就必然会对宋人王延德《西州使程记》称高昌回鹘“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录、黠戛斯、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以及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有关“回鹘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某词是“国家之名”等记载难以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法”。

另有学者著称,回鹘在菩萨任酋长时期便“开始以独立的、具有较强大军事力量的一个民族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书中不仅使用了“回鹘族”等概念,且开篇第一句话就称:“回鹘,是今天维吾尔族、裕固族的共同祖先。”给人的印象是:现代的维吾尔族、裕固族是由古代的回鹘族分化发展而来的,即回鹘是老子“族”,而维吾尔族和裕固族是儿子“族”。以笔者之见,将“共同祖先”改为“重要族源”,将“回鹘族”改为“回鹘集团”或“回鹘汗国”要更为妥当。持以上观点的学者往往以“古代民族”的概念定义之,以示与“近代民族”或“现代民族”相区别,但“古代民族”的概念至今也不曾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就语言而论,姑且不说其内部还包含有印欧语部落、蒙古语部落、东胡语(通古斯-满语族)部落和大量的汉人,单就突厥语部落的方言而言便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普遍存在于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等诸层面;就文化而言,诸部落的习俗和文化心理也多有不同。正为此,在克普恰克人(qïpʧaqlar)建立的东突厥汗国统治时期,九姓乌古斯(toquz oʁuz)诸部落便时常反叛,《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磨延啜碑》、《阙特勤碑》《铁尔痕碑》、《铁兹碑》、《毗伽可汗碑》等刻写于东突厥汗国时期的突厥语碑铭中对此都有大量记载。可见,匈奴、突厥和回鹘实质上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权名称。与其使用“回鹘族”这一模糊概念,倒不如使用血缘性的“氏族”、“部落”、“部族”和政治性的“部落集团”、“部落联合体”、“汗国”、“王朝”等不同范畴的概念。这一观点,笔者早在1999年便已提出。遗憾的是,上述概念直到今天仍为许多学者的论著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