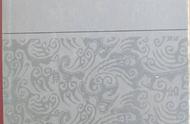婆家的年夜饭
"老姑爷回来了!还带着城里媳妇回来过年啦!"村口的喊声传来,我的心一阵发紧,向丈夫投去求助的目光。
那是二〇〇一年的春节前夕,结婚十年,我第一次踏进了婆家的门槛。
一路上,我的心情如同东北的天气,阴晴不定。窗外飞速掠过的白桦树和苍茫的雪原,让我的心绪更加飘忽不定。
我叫李嘉仪,是县城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我丈夫张明河是我大学同学,我们毕业后一起留在了城里,他在国棉三厂工作,我则在学校教书。
那时的日子,虽不算富足,但也有滋有味。我们住在单位分的四十平米的小楼房里,阳台上晾着我们的衣服,客厅里摆着托人从省城买来的二十一寸彩电,厨房的水槽边放着生锈的铝制脸盆。
每天早上,我赶在六点半出门,骑着二八自行车穿过晨雾,赶到学校批改作业。丈夫则背着"红旗"牌饭盒,踩着工厂的汽笛声准时上班。
忙碌的工作和照顾孩子的重担让我很少有时间回农村老家,更别提丈夫远在百里之外的村子了。车厢里的暖气有些过热,我解开羽绒服的拉链,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荒凉景色,思绪飞到了过去。
记得刚结婚那几年,每到春节,婆婆总会托送煤的师傅带信来,后来村里装了一部手摇电话,她就会打电话过来,那头是充满期待的声音:"嘉仪啊,今年能回来过年不?"
我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孩子太小啦,学校有事啦,父母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啦。电话那头,婆婆总是温和地说:"没事,你们忙你们的,有时间再说。"

可每次过完年,我们家的门铃总会响起。打开门,是邮递员送来的包裹,里面装着婆婆亲手做的腌菜、红薯干和一些土特产。包裹上的绳子总是打着复杂的结,仿佛是怕路上散开,包装纸上写着歪歪扭扭的地址,那是婆婆请村里小学老师写的。
车窗外,北方的冬天光秃秃的,田野上覆盖着厚厚的雪,偶尔有几棵枯树在寒风中摇曳,远处的小山包像一个个蜷缩的老人。我心里揣着忐忑,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十年来从未谋面的婆家。
丈夫倒是一副轻松的样子,哼着不成调的小曲,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打着节拍。他今年的心情似乎格外好,眼睛里闪烁着我许久未见的光芒。
"你看,那里就是我长大的村子。"丈夫忽然指着窗外说,声音里带着掩不住的自豪。顺着他的手指,我看到远处的一片灰白色的房屋,炊烟袅袅升起,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温暖。
汽车在村口停下,我们拎着大包小包走向村子。路两旁的大爷大妈们纷纷探出头来,打量着这对"城里人"。孩子们则好奇地围过来,盯着我们的行李,眼睛里满是羡慕。
"明河啊,这是你媳妇吧?长得真俊!"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大爷冲我们喊道。丈夫笑着点点头,我则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你婆婆这些日子可念叨你们了,天天去村口等呢!"另一位大娘接着说,声音里带着几分埋怨。我的心里又是一阵愧疚。
走了约莫十分钟,丈夫停在一座青砖瓦房前,推开了那扇已经掉漆的木门:"到家了。"

院子里摆满了东西,有装在竹篮里的鸡蛋,用红纸包着的苹果,还有几袋大米和面粉,甚至还有一只拴在角落里的大公鸡,见到陌生人,扑腾着翅膀"喔喔"直叫。
婆婆站在堂屋门口,头上的银发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光。她比我想象中的要瘦小,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腰间系着一条已经褪色的围裙,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
那双手粗糙得像树皮,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土,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她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我和丈夫的结婚照,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但被擦拭得很干净。
"娘,我们回来了。"丈夫上前拥抱了她。我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直到婆婆转向我,脸上堆满了笑容:"嘉仪,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的眼眶顿时湿润了。她叫我的名字时,声音里充满了熟悉感,仿佛我们已经朝夕相处多年。
"快进屋,外面冷。"婆婆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走。她的手心温暖粗糙,传递着一种无言的力量。
堂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八仙桌,四把木椅,墙角是一台老式柜式收音机,桌上摆着几个苹果和一包"大前门"香烟,那是丈夫最爱抽的牌子。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气味,是干柴、土炕和老物件混合的味道,这是我记忆中外婆家的气息,一种让人安心的乡村气息。
丈夫去厨房帮忙,留下我和婆婆在屋里。她拉着我坐下,不断地给我倒热水,嘴里念叨着:"城里冷不冷?孩子上学怎么样?吃的习惯吗?"
这些琐碎的问题,平常被我视为唠叨,如今听来却倍感温暖。我一一回答着,注意到婆婆眼角的皱纹随着我的每一句话而舒展开来。

"娘,这些年我一直没空回来看您,对不起。"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这句话。
婆婆摆摆手:"傻孩子,说啥呢。你们在城里工作,能有啥空啊。再说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院子里那些东西..."我欲言又止。
"那是村里人知道你要回来,特意送来的。"婆婆笑着解释,"大家都说,明河娶了个教书的媳妇,可有面子了,得好好招待招待。"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感到一股暖流从心底涌出。这十年来,我从未想过,在这个我从未踏足的村庄,有这么多人挂念着我,关心着我。
晚饭是一桌丰盛的家常菜。婆婆做的每一道菜都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酸菜炖肉,土豆丝,拌凉菜,还有一碗热腾腾的鸡汤。
"这鸡是村东头老刘家养的,下蛋特勤快那只,知道你要回来,硬是送来了。"婆婆边给我夹菜边说,"这些年,你在城里忙,家里的事情也没帮上忙,别有心理负担。"
饭后,我主动收拾碗筷。柴火灶上的铁锅里还冒着热气,灶膛里的火苗跳动着,发出"噼啪"的声响。在厨房忙活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旧木箱,上面落了一层薄灰。
好奇心驱使我打开了它。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叠信件和照片。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封,竟是我多年前寄给婆婆的。信封已经有些破损,但里面的信纸却保存完好。
"婆婆,您好!我和明河最近都挺好的,就是工作忙了点。城里的冬天不如村里冷,但也挺难熬的..."我自己都记不清写过这些话,却被婆婆珍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