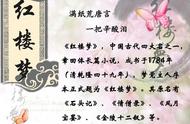苏东坡不仅是宋代一等一的全才型文化巨人,就在整个中华历史里,也能列入知名度最高的古人前列。以今时今日人们对苏东坡的喜爱和关注,多数人也知道他的一生不算顺遂。尽管宋神宗与宋哲宗两代皇帝对他其实都有好感,偏偏还是将他贬来贬去,连带儿子们也一起颠沛流离。对于著名的四川眉山三苏,今天人们大多都知道苏轼和苏辙兄弟俩感情非常深厚,却很少有人关注苏东坡三个儿子的经历。实际苏迈、苏迨与苏过,全都因为苏东坡后半生的贬谪,改写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苏东坡塑像
一、长子苏迈受乌台诗案牵连
苏迈,字维康,是苏东坡第一个王夫人王弗所生,按籍贯是眉州眉山县人,实际生于北宋的京师开封府。五岁左右,因苏洵过世,苏轼、苏辙兄弟将父亲送归眉山安葬,苏迈跟着家人一起回到四川,在守孝期间跟着父亲读书三四年。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苏轼守丧结束。夫人王弗身故,苏轼带着不到十岁的苏迈回到开封,续娶妻子的堂妹王闰之,将苏迈交给王氏抚养,督促读书。这时,王安石推动新法,苏轼有些不赞同(实际苏轼一生对神宗年间新法的态度有过几番转变,但他并不回避自己的态度,这也是造成半生跌宕的原因),于熙宁三年写了著名的上皇帝书,跟着还再论、三论。
苏轼在仁宗末年的科举中一战成名,受欧阳修大赞,王安石和神宗其实都对苏轼很欣赏,四川老乡范镇就想推荐苏轼接替知谏院,王安石坚决阻止。即便如此,神宗还想安排苏轼编撰史书一类闲散职务,可以留在京师,但王安石以提升待遇的方式非要将其派往杭州,苏迈跟着前往。三年后转去密州,苏迈就跟随父亲辗转,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年。
熙宁十年(1077),苏迈满十八岁,苏轼为儿子向同乡前辈吕陶求亲(为四川眉州彭山县人,年长苏轼十岁。吕陶是宋代典型弘扬儒学的士大夫,重视民生和文化教育。本来在四川知彭州,也上疏反对王安石,贬为蜀州通判。宋哲宗继位后因司马光等人恢复地位,改殿中侍御史。活到徽宗年间身故,享年七十七岁。另外,苏轼最初想的是通过范镇向司马光求亲,都知道司马光只有一个夫人张氏,一说张氏没有生育,一说有过两个夭折的幼子,最后才以哥哥司马旦的儿子司马康为嗣子。并没有关于女儿的记载,所以苏轼向司马光求亲一事颇耐人寻味,很有苏轼初回京师希望表明立场,结好司马光的意思。苏轼、苏辙在京师参加制科考试时,司马光是考官,所以苏轼苏辙等同于司马光的门生。苏洵过世时,司马光参加吊唁,苏轼顺便为亡母程氏向司马光求墓志铭,司马光欣然同意。所以本来司马光与苏轼兄弟交情也匪浅,因此有希望结亲巩固关系,至于是否司马光本人女儿恐怕都不要紧,但这一事没有顺利达成):“里门之游,笃于早岁;交朋之分,重于世姻。某长子迈,天资朴鲁,近凭一艺于师传。贤小娘子姆训夙成,远有万石之家法。聊申不腆之币,愿结无穷之欢。”两家结亲,次年八月,吕氏生下儿子苏箪。三年后,苏迈考中元丰四年(1081)进士,次年吕氏病故于黄州。

司马光画像
就在苏迈积极备考的元丰初年,苏轼卷入著名的乌台案中。苏迈当时在京师,天天给狱中的苏轼送饭。父子俩不能直接见面,于是暗中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坏消息就送鱼,以便心中有数,同时,苏迈为父亲的案情还四处奔走,托人申诉。
关于乌台案的研究已经很多,大体是苏轼辗转杭州、密州、湖州等地为官时,亲眼目睹新法推行中,尤其青苗法、食盐专卖法等令百姓利益受损。苏轼为人正直,就在诗歌里有所感慨。
乌台案之所以严重,和王安石本人却没关系。王安石于熙宁九年就因为舆论被免,新法后期是神宗一手坚持推行,所以,对苏轼的调查是钦定,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针对苏轼。
他们从苏轼在湖州的上书中找麻烦,然后联系一系列诗歌找出大不敬的证据,尤其苏东坡和李清臣、司马光、苏辙、黄庭坚等人来往唱和的作品。另有和驸马王诜的往来文书是重点,苏轼在湖州为官,正是王诜先从开封得到消息,通知在南京的苏辙(指宋代南京,今河南商丘市)。
通过审理,苏轼最终承认一些作品涉及新法,因此宋神宗十分恼怒,大理寺根据宋代刑律中批评君主的量刑,苏轼属于士大夫文化的“讥讽”,表示婉转反对,情节相对较轻,加上认罪态度也不错,按律应“徒二年”。再根据宋代另一“会赦当原”的原则,就是创作一系列诗文的时间段,每每有大赦天下的诏旨颁布。诗文批评并不是十分过激,属于可以原谅的范围,归纳下来,还是可以免除对苏轼进行惩罚。

影视剧中的苏东坡形象
御史台对此不满,又让审刑院复核案情,得出结论是支持大理寺,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可都知道,苏轼最终还是被贬,实际就是另据皇帝圣旨对苏轼要处以“特责”,从法律角度本可赦免,但皇帝另外强加惩罚。如推行新法之初,苏轼批评激烈一点或早被发现态度如此,那就属于大不敬之罪,尺度严一些处以死刑都是可能的,好比当年韩愈激烈反对唐宪宗迎佛骨,一开始就被论罪当死 。
由于苏轼在朝野上下有很多人欣赏,不论是出于苏迈苏辙的请托,还是本来就同情,先后有很多人求情。像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连王安石实际也爱惜苏轼,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更有太皇太后曹氏出面:“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之可乎?”还有章惇也出面说情(章惇和苏轼同是嘉祐二年进士,一起从陕西出仕,苏轼为凤翔判官,章惇为商州令,两人同游终南山。苏轼贬谪期间,章惇多次送衣物药品,因这份情义,苏轼后长期与章惇保持来往。两人关系变坏是哲宗以后,朝中仅剩章惇一个所谓新派,苏辙在司马光等人集体批评时率先附和打击章惇,苏轼当时选择沉默。章惇为人冲动强硬,对苏轼一声不吭感到失望。后来哲宗亲自主事重用章惇,再次贬谪苏轼。但徽宗继位后反过来贬章惇到岭南雷州,苏轼回到中原曾给章惇和儿子章援去信,同样送去一些药物,两人关系有所缓和,但再没有机会重遇。苏轼死后过了四年,章惇也死了),最终苏轼贬谪“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长子苏迈和父亲一起到黄州。
其他有三人受牵连很重,首推驸马王诜,因泄密给苏轼,还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更因对公主不礼貌,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为真宗名相王旦的孙子,官职并不高,但是有名画家,和苏轼感情很好。其父王素也对苏轼很欣赏,王素与苏轼的伯乐张方平同龄,张方平正是王巩的岳父。苏轼守父丧归蜀期间,王素知成都府,苏轼就曾登门拜会。王素于熙宁六年身故,年六十七),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宾州(今广西宾阳)。苏轼非常内疚,写诗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元丰四年(1081),苏轼有《次韵和王巩六首》,之后多次在书信中流露愧对王巩的自责之意。
第三个是弟弟苏辙,曾奏请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由于亲属连带关系,苏辙降职任筠州酒监(宋代筠州在江西省,位于高安县一带),称“五年不得调”。不无凑巧,后哲宗主事绍圣年间“绍述熙宁”,苏辙因批评李清臣在科考试题中拿新法做文章惹怒哲宗,贬袁州知州,还没有到袁州就改为分司南京(宋代南京为河南商丘),又令筠州居住。苏辙加深对颜回安贫乐道的体会,写了著名的《东轩记》回忆父兄均爱竹,力求品格高洁的志向。
元丰七年(1084),苏迈和苏轼离开黄州到江西境内分别。当时苏迈授饶州(今江西省鄱阳湖东)府德兴县尉,父子二人在齐安湖口石钟山下,一起实地考察,苏轼写下流传千古的《石钟山记》。之前在黄州,苏迈就对鄱阳湖畔的石钟山来历十分费解,翻阅《水经注》等记载,苏轼坚持他的名言“博观约取”,需要多看书,但不能被书所误,有时要做考察。之后苏迈前往德兴县赴任。
与苏迈分别后,苏轼到筠州探望苏辙(也有说先探望苏辙,然后苏轼再和儿子苏迈分别),两人同游览附近山寺。然后苏轼去了庐山,留下充满禅学和哲理的“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体悟,这一次庐山之行被誉为苏轼一生悟道的转折点。江西是南方禅宗中心,苏轼和苏辙都留下重要的思想转变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