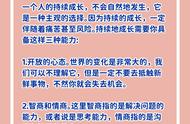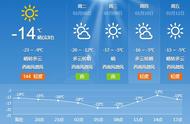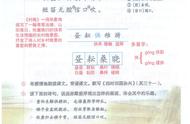图一 奉华款汝窑纸搥瓶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以实物观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汝窑纸搥瓶(图一、图二)原本应有盘口,由于口沿破损被磨平至颈部。同样,故宫博物院藏钧窑天蓝釉渣斗式花盆的上半部因残而被磨掉口沿,由此表明将珍贵瓷器打磨甚至改变形状以保全瓷器的做法在宫廷并不少见。
对器物不平不稳处,通过打磨进行调整:“乾隆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副催总六十七持来司库郎正培、副司库瑞保押帖一件,内开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太监胡世杰交来定磁枕一件。传旨:将枕底磨平钦

图二天青釉纸搥瓶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对缺釉的器壁进行磨平抛光,例如:“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十九日,郎中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青花白地双环耳瓶一件。传旨:将此瓶缺釉处磨好,钦此。24”“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来说,太监如意交铜镶口底足雾红碗一件,木座;青绿双环瓶一件,木座。传旨:俱交苏州将碗所镶口里边照外边窄口一样另镶,其青绿瓶工颜色磨平上亮送来,钦此。25”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南宋官窑方花盆(图三,高9.2厘米,口径15.3厘米,镶镀金铜口。通过仔细观察可知,器底渗水孔的边缘露胎且有打磨痕迹,说明此孔并非在烧造时即存在,而是后钻磨出的。器底外部同样有露胎和精细的打磨痕迹,这是原有的四个足的位置。口沿已镶嵌镀金铜边,从工艺来看属于清代釦边工艺,而在釦边之前该器的口沿是否被研磨过未经检测尚不得证实。不过器物底部的痕迹已明显表明,该器原本底部无孔并不是花盆,根据已知考古材料也没有发现南宋官窑带孔的花盆器物。那么为何后人要将如此贵重的瓷器底足磨平并钻孔呢?可以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该器的拥有者主动改造器型,以达到作为花盆的实用目的;另一种是底足在使用中被损坏,因难以复原而失去了原有功能,所以将其打磨成花盆继续使用。就南宋官窑的珍贵程度来衡量,第二种可能性更大。虽然目前受材料所限,无法核实这件器物被改造的时问,不过从镶镀金铜边和器物本身来分析,这件官窑瓷器受到了宫廷相当的重视,以尚古又追求完美的乾隆皇帝的性情来说,不会在贵重的高古瓷器上做此类功能型的改动,因此推测这样的改动可能发生在乾隆朝之前。


北宋汝窑青瓷胆瓶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3.镶釦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已开始使用釦边漆器。《说文》曰:“釦,金饰器口。26”“这种用金、银、铜等金属箍镶器口的做法不仅能牢固器物口沿,延长使用寿命,而且能起到装饰作用,彰显了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大约于五代镶金属釦技术在瓷器上流行开来,尤其适用于因发明覆烧技术而产生“芒口”缺陷的定窑瓷器,以致镶金属边至今成为定瓷的标志特征。
依照清宫档案和传世实物,釦边器物多为贵重的高古瓷器,以汝窑、官窑、哥窑、定窑瓷器为多,也有少量明代和本朝的单色釉、青花瓷器。在瓷器釦边中最为常见的是“镶铜口、铜足”,更为珍贵的器物使用“镶铜镀金”、“镶银镀金”,仅有少量瓷器被录为“镶金口”。实际上从实物情况和操作工艺来看,“镶金口”并非釦金边,而应属于镶铜或镶铜后镀金釦。“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催长四德、笔帖式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汝窑猫食盆一件,欲镶金口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厂奉旨:著镶薄些,铜扣烧古,钦此。27”文献所述的“汝窑猫食盆”即为汝窑水仙盆,现在传世汝窑水仙盆中口沿镶铜釦的有两件,分别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图四),但前者在当时被乾隆皇帝认为是官窑,由此大阪藏汝窑水仙盆很有可能正对应这条文献提到的猫食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