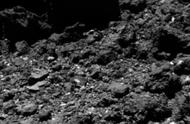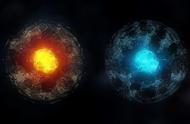1.在分析语言如何描述世界的问题时,维特根斯坦发现我们使用的语言存在很大的问题。即便是符合逻辑的语言,也不能令人满意的描述世界,原因是包括逻辑语言在内的任何语言都是有限度的,这就是语言界限的思想。
2.维特根斯坦明确了语言的界限就是可说与不可说的,在这界限之内的东西是可以言说的,而在界限之外的东西是不可言说的,即保持沉默。
3.维特根斯坦认为即使是不可说的也能通过显示的作用帮助我们理解。他反对将不可说的东西说出来,对待哲学的正确方法也就是这样,除了与哲学无关的问题之外不再说什么。
4.维特根斯坦进而指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就在于试图说出不可说的东西。他的“不可说”清楚了形而上学存在的根基,使之成为无根的浮萍。
后现代转向
十二、福柯:“人之死”与“知识型”

1.福柯关于“人之死”的论断,其实是在“知识型”的考察中得出来的。所谓“知识型”就是组织和决定知识形式和方法的框架,是隐含在知识下面的深层结构,福柯认为,在西方文化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知识型”。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型”不断变换的历史。
2.福柯将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即“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现代时期”。分别对应“相似”知识型、“表象型”知识型、“根源”知识型。“人”的诞生是现代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意味着全部知识归根到底来自于人,人成为知识的王者,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
3.如果说“人的诞生”是“知识型”变化的后果,“现代知识型”造就了“人”,那么,很容易预见一个事实:当代“知识型”再次变化将导致“人”的死亡,“人”将不不再处于创造的中心地位。
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
十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

1.霍克海默、阿多诺把西方文明理性传统的“启蒙”的内涵扩展为人类一般的进步理想。根本目标是使人类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2.启蒙辩证法:启蒙走向反面,启蒙的目标是要祛除神话,启蒙理性本身却变成了神话;启蒙要是人摆脱对自然物的恐惧,却陷入对自然总体性的恐惧;启蒙高扬人的主体性,但“被彻底启蒙的人类丧失了自我”;启蒙反对暴政,但启蒙造就了新的暴政;启蒙崇尚理性,带来实惠的进步,却同时伴随着人性的堕落;启蒙“提高人的材质的同时,也是人变得更加愚蠢”,“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
3.启蒙的本质是作为“支配”力量的“主人精神”。达到用理性的正义来取代申花的非正义。而“支配”正是导致启蒙倒退的内在因素。启蒙的工作是从祛除神话对人的支配开始,认为启蒙可以祛除神话,则视世界为透明的和可控的,相信理性不仅可以通过知识掌握世界,也可以通过理性利用世界和控制世界,这就招致了启蒙所要反对的神话和信仰的复辟,即创造了对理性无所不能的新的神话。神话变成了启蒙,启蒙又变成了神话,这就是启蒙的逻辑。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以启蒙名义进步的文化工业,实际是对大众的欺骗。旨在追求解放的启蒙如何反而深深陷入了野蛮状态。以便把启蒙从盲目同志的纠结中解脱出来。
十四、卢卡奇:历史性与总体性

1.卢卡奇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历史概念,历史是其哲学的逻辑出发点。卢卡奇用历史的方法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必须是本体论的,进而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历史真正被理解为一种方法,一种不仅审视哲学本身,也是审视所有事物的方法,所有问题只有从历史理论出发,才能得以真正解决。站在总体性角度,通过历史的维度来审视一切。
2.卢卡奇从历史逻辑出发,以历史的方法解释存在并进一步解释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本体,自然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从而社会存在和自然存在统一于历史的方法中。历史性是一切社会存在的根本范畴,而一切存在都是社会存在。
3.历史是主客体之间的辩证运动,历史作为客体不是与主体无关的客体,而是主体的产物;作为实体的历史也可以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卢卡奇认为历史的主体就是人们创造世界的活动。
4.历史的本质是实践,存在本身不是自然客体,而是社会客体,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才使得历史具有了主客交互作用的生成性的建构力量,这也表现了历史的本质。
十五、杜威:工具主义与实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