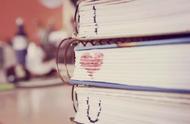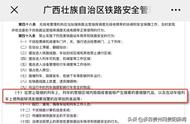糖-------程兆强
由于担心吃甜会给身体带来危害,现在许多人已经不喜欢吃糖了,就是那些天生爱吃糖的孩子,在父母的严格管束下也很少吃糖,而两岁以下的儿童更是已被家长禁止吃糖。我小的时候不是这样,那时不仅孩子们爱吃糖,就是大人也喜欢吃,并且糖还是走亲访友、馈赠友人的上好礼物。
我说的糖是指块糖,就是那种用花花绿绿彩纸包着的糖,老济南人称它“花糖”。记得我小时候吃的糖,多是济南当地产的水果糖、酥心糖、高粱饴和牛奶糖,也吃过外地产的,是上海的“大白兔”奶糖,不过没有吃过几回。“大白兔”奶糖很有名,听说当年*总理爱吃这种糖,总理日理万机,工作到深夜是常事,他常常阻止工作人员为他加餐,吃一颗“大白兔”糖,算是给身体补充一点能量。并且,周总理还曾把“大白兔”奶糖当礼品,赠送给来访的外国友人。
我喜欢水果糖,手指头大小,果香浓厚,特别是一种桔子味的糖,尤其讨人喜欢。这种糖晶亮透明,质地坚硬,含到嘴里化得慢,甜香经久。还有,买这种水果糖很划算,它身量小,一斤能称一百零几颗,一块多钱一斤,一分钱能买一颗。那时,孩子哭闹了,父母哄孩子,会拿一颗糖塞到小孩嘴里,或者给那大一些的孩子两三分钱,让他们到副食店里买。这样的招数哄孩子,非常管用。我在一个商业部门工作过,那时单位上经常组织职工技术比武,一位同事称重包糖技术高明,是单位的“技术能手”,多次代表单位参加上一级的比武大赛,他称一斤花糖只抓两把,上下差不了一两颗,有同事给他取了个“两把准”的外号。
说起称花糖,我想起前年去北京的一件事。一天,我去王府井逛街,当走到王府井百货商场时,忽然想起当年“一抓准、一口清”的劳模张秉贵,便抬脚进了商场。在一楼,商场专门设立了“张秉贵纪念馆”,我仔细观看了所有展品。望着张秉贵的塑像,我停留许久,这位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以满腔的热情和精炼的技艺,不知接待过多少顾客,不知卖出过多少糖果,亦不知有多少游客慕名来到这里,看这位德艺双馨的名人,同时也买一些糖果带回自己的家乡。我喜欢水果硬糖,不全是因为水果糖比牛奶糖、酥心糖出奇好吃,而是它的价格要比别的糖便宜一些,同样一毛钱,买水果糖能买十颗,而买牛奶糖、酥心糖只能买六颗。还有一点,牛奶糖、酥心糖不经化,放到嘴里一会儿就融化没了,水果糖却能化好长时间,享受甜味好长时间。不过牛奶糖的奶香味、酥心糖的花生味也很诱人,闻到香味就让人口生涎水。
我说的是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人们吃糖的事。再往前追溯,是我听人说或是从书本上看的。我记得曾看过一份资料,说济南最早的糖果店是普利门街的“老茂生糖果庄”,是天津老茂生的分号,掌柜的名字叫薛宝生,所卖的糖果是自产的水果糖。从这点上看,当时济南还没有生产糖果的厂家,后来济南糖果业快速发展,仅糖果厂就有好几家。
父亲曾给我讲过他幼时的事。那时正是日伪时期,日军侵占济南期间,出于麻痹和奴化中国人,常常装出一副副亲善友好的样子,见到中国孩子,会拿出一两颗“洋糖”送给他们吃。可那些孩子一见到身着戎装、持枪挎刀的日本军人就害怕,常常是面对眼前的糖块,既不想伸手接又不敢不去接,左右为难,有的孩子吓得直哭。喜欢吃糖是孩子的天性,吃糖本该是一件快乐的事,可沦陷区的孩子,面对持枪的日本军人和喜欢吃的糖块,却是两难选择,他们太委屈、太可怜了。是他们父母的不争气,没守护好自己的家园,让强盗进了家门,让幼小的他们遭受了这般的苦痛。
现在人们不喜欢吃糖,以前人们却是那样喜欢吃糖。以前过年的时候,孩子们给邻家长辈去拜年,得到的回报是一捧爱吃的糖块;以前农村里娶媳妇,婚礼行将结束时,会向现场抛出一把把喜糖,招致人们快乐的哄抢。就是在七、八年前,我还在济南英雄山文化市场看到一个福建人,手里提着一个大纸袋,一边向人分发红红绿绿的糖块,一边笑不拢嘴地告诉人家,自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请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快乐。
时代不停歇地前进,事物不间断地变化。如今,许多人不喜欢吃糖了,而我仍喜欢吃糖,我觉得糖能带来浓浓的甜滋味,吃糖能让人快乐。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我要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