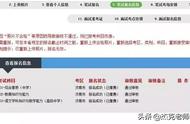一碗喷香的鸡汤泡炒米,绝对是安庆人的舌尖招牌。鸡肉酥烂脱骨,鸡汤清亮鲜美,一把酥脆的炒米,简直神来之笔,素朴的鸡汤,仿佛有了灵魂。

清人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鸡功最巨,诸菜赖之。”古往今来,鸡肉的吃法多样,从南至北,由东到西,不同地域,吃鸡方式各不相同,蒸煮炸炒烤,十八般烹饪手法,尽展舌尖真功夫,花哨吃法背后,无不充满对生活的满腔热爱。
食物有根,什么样的土地,就长出什么样的滋味。安庆,地处长江之畔,江湖山野交融,使得安庆人的饭桌山江兼容、水陆毕陈,每一道佳肴独具风味,令人回味无穷。
在吃鸡这件事情上,安庆人做法也花哨,不过,一道看似素朴的鸡汤泡炒米,却最“鲜”声夺人,成为刻在每个安庆人DNA里的家味。

陶罐煨鸡,是安庆农村地区最家常的烹饪手法,充满农耕智慧。不知道这种原始的烹饪方式源自哪一代,母亲是从家婆那里学会的,家婆又从她的母亲那里耳濡目染,于是伴随家味代代传承至今。一个陶罐,一瓢清水,一只散养土鸡,任由柴火灶膛里燃烧未尽的炭火煨上几个时辰,看似粗糙的烹制方式却最大程度激活了土鸡的鲜香滋味。

光秃秃的鸡汤未免寡淡,地里新收割的稻米派上了用场,脱壳的新米,在锅中翻炒至焦黄,锅气裹着柴火的烟味,赋予炒米另一重滋味。炒米,本是用来打尖的,相传,江西移民迁入安庆时,将炒熟的米作为干粮携带,用于充饥。炒米可干吃,可做成炒米糖,还可做成糖水鸡蛋泡炒米,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是安庆农家人用来待客的重要茶点。可是,无论怎么吃,仿佛都差点意思,直到遇见一碗热腾腾的鸡汤,鲜与香得到双重升华,鲜香味美的鸡汤泡炒米成为安庆人舌尖上的“地标”美食,饱含一代代安庆人对故乡的深情厚谊。
记忆里,每逢佳节喜事,或者家中来了重要客人,尤其春节期间,这道承载了主人的热情与诚意的鸡汤泡炒米必不可少,时至今日,依旧是安庆人喜宴、家宴上的“重头戏”。
小时候,农村生活清苦,母亲怕我们营养跟不上,鸡汤泡炒米成为儿时记忆里最常出现的美味。那时,在县城读高中,月末回家,母亲总是第一时间从灶膛里掏出黢黑的陶罐,扒拉着夹出鸡腿放进碗中,再倒上油亮亮的鸡汤,撒上一把焦黄的炒米,香味诱人,迫不及待大口吃起来,泡了鸡汤的炒米,那股充溢口腔的浓香,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总是把最精华的部分留给子女,她的碗里,总是些内脏、鸡头和鸡爪,劝她吃些好的,她总用“我喜欢吃这些”搪塞而过。这份深沉的母爱,是记忆里这碗鸡汤泡炒米最温暖的底色。

长大后,吃过无数回城市版的鸡汤泡炒米,却总也找不到那时的味道。才发现,小小一碗鸡汤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缺一味元素,或者稍有偏差都差点意思。
安庆农家鸡汤泡炒米,用的是散养的土鸡,土鸡吃的是谷物草虫,每日奔跑于林下草地,肉质紧实鲜嫩、富含营养;烹饪方法得用陶罐和土灶,陶罐盛鸡,柴火慢煨,这是现代炊具无法复刻的精妙;点睛之笔,是那一把自家地里头收割的稻米,在柴火灶上翻炒至焦香酥脆的炒米。最素朴的用材选料,最接地气的烹饪方式,才是安庆人记忆深处那碗鸡汤的精髓所在。
舌尖风味,是家乡风土人情的缩影,沉淀的是厚重的乡愁情结。如今,安庆广大农村越来越空,离乡人如同候鸟般在城市与家乡之间来回“迁徙”,好在每次回家时,饭桌上总有不变的家常滋味,那碗鸡汤泡炒米,是对归家的人最诚意的迎接仪式,腾腾热气里,是直抵心灵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