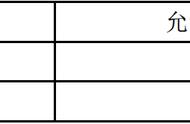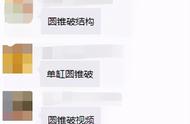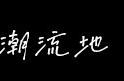潘祖荫“伯氏吹埙”花笺

潘祖荫“伯氏吹埙”花笺

潘祖荫“伯氏吹埙”花笺
可惜笔者手边没有潘祖荫的书,否则应该能找到一些来自他的直接记载。
这件事情还没有完。
过了一百二十多年,2008年有音乐学者对这些“太室埙”做了专门研究。
研究发现,这些有“命(又释作令)司乐作太室埙”七字铭文的“太室埙”,迄今在全国博物馆共发现八件,上博、故宫各一件,还有六件全在山东省博物馆,八件埙全部来自个人捐赠,无一考古出土发现。
又经过实测发现,这些埙上的开孔呈V形排列,埙的指孔设计与考古发现商周埙常见的倒品字形排列截然相反,不如商周埙指法自然;而且这种埙孔排列方式违反乐器发生原理,实际吹试没有一件能够发出声音。
第三,“太室埙”铭文中的“太”“室”“埙”三字均有疑点,特别“室”字篆文非常别扭奇怪,因此上博在有关书里将这个字释为“宰”字,其实同样牵强。

上海博物馆藏“太室埙”及铭文拓片
还有,这些“太室埙”均为捏制,形制比较粗糙,与多为轮制且光平规整的商周埙完全不同。
根据这些研究,学者对这些“太室埙”疑点重重,认为均“应疑为伪作”。(参见方建军《太室埙、韶埙新探》,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 年第3期。)
稍后,又有文献学者对先秦古籍《周礼》中“大司乐”的官名提出疑问,认为该官名仅出现于《周礼》一书中,没有得到其他先秦文献乃至金文石刻等文字的印证,孤掌难鸣。也就是说,周代根本没有“大司乐”这一官职,该学者更进一步提出,周代乐官之长应为“乐正”而非“大司乐”。(王红娟《周代乐官之长正名》,原载《文艺评论》,2011年2期。)
还有研究披露,说这批土埙都是王懿荣家乡好友尹彭寿(字慈经,号茂才)提供的,此人兼有金石学者和古董商双重身份。这就更令人可疑了。
综合上述研究,这种所谓的“太室埙”,估计就是古董商为了射利,绞尽脑汁,故意做出来给这些好古成癖的收藏大V们“定向投喂”的。饶是潘祖荫、吴云和赵烈文等人精鉴如此,也难免上当。
本来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不料网上随手下单的《王懿荣往还书札》(凤凰出版社,2021年8月)火速到家,翻开一看更是大吃一惊。
原来那年春天,王懿荣回山东,还去陈介祺家里住了三天,饱览他的新近收藏,谈古论今,非常快乐。
三月份回到北京,王懿荣写了封信给陈介祺,里面提到:“郑堪(按即潘祖荫)得三埙及各匋完器数事,则皆齐人之诈,而南人不复返矣,又不能实言之也……”(三月廿九日,页90)估计他们见面时就讨论过此器。
过了半个月,王懿荣专门写信谈这些土埙:
寿翁世姻伯大人:
侄于四月十五日由京启行,濒行,尹慈经茂才又寄一埙来,文与前不同,乃“韶”埙也,文剧佳,而质破,同时渠并寄一枚与潘郑堪先生,却完整,文与此同,似有剔痕(见拓本便知,器却真,与侄一相同,恐或无字,渠仿之,不必言,见拓本自知),不如此之精也。
侄每见东物外出,心必作恶数日。渠所得太室文三埙(有阳文)则伪者,大小不等,荣亦得此伪者四,回京寄呈,一笑。(皆从侄一器繙沙,且作阳文)潘乃大喜,寄银与尹,属多购东物。此吾齐乐器,明明有“韶”字(潘释“昭”字,非,若告以此字,东物无噍类矣),纷纷为外人所有,则可惜也。请加以物色之。青州河岸所出,尹(此公好外交)寄潘信言尚有异文者,不知何等。即颂颐安。侄懿荣顿首,四月望日倚装。(同书,页90-91)
两封信里的意思说得很清楚,所谓“太室埙”都是假的,是从他一个器物上翻砂伪造的。而有“韶”字的土埙,器是真的,文字是仿的,是后加上去的。这些东西都是尹彭寿那边的人伪造的。另外,王懿荣家乡观念很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浓厚,似乎很不愿意山东家乡的古物(东物)外流,哪怕是自己的老师。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韶”埙,下腹部钤印铭文“令作韶埙”,也是潘祖荫旧藏,估计就是王懿荣信中指称的那枚。此埙2018年底在苏州博物馆《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收藏特展》上曾公开展出过,经测定,此埙可构成徵-宫-商-角-清角-徵的音阶结构,音色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