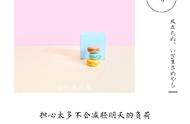《繁花》番外短片《好久不见》里以《花样年华》2000年的上海首映为契机,阿宝和汪小姐得以重逢。
用王家卫的话来讲,这是发生在香港、上海两个不同城市间的同样的“花样年华”,同样关于错过,同样关于言语“不响”中,心底无数暗流细细密密地流逝。
上海是王家卫的乡愁,5岁他随父母移居香港,与留在故乡的哥哥姐姐分离,一家人住在上海人的聚居地。时代里注定飘零的人,被历史的巨浪打翻冲散,再席卷上岸,心里想的是:总有一天会回去。《花样年华》的灵感来源——刘以鬯的小说《对倒》中同样惆怅弥漫。于是,世事无常里总有刻意为之的“不变”的保留,是在香港这座孤岛上,再建一座孤立的文化堡垒:方言私语、旗袍、高耸的发髻、无线电、标记四季的时蔬饭菜、灯影迷离的麻将席……是封存往昔的古迹现场,像一枚包裹着昆虫尸体的淡黄色的琥珀。

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刘以鬯小说《对倒》打出了《花样年华》灵感来源的宣传语。
上海记忆被嵌套进香港的都市梦游中,这个空间,是《花样年华》故事发生的起点。王家卫曾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谈道:“我想唤回从前的那些记忆,我害怕这些东西以后我会忘记……我绝对不是要精准地将60年代重现,我只是想描绘一些心目中主观记忆的情景。”如果说《花样年华》是王家卫对童年时光的追忆和变形,《繁花》则是他成长过程中,记忆拼图里缺失的那重要的一块,是长久地,匮乏地、深情地凝望平行空间里另一种生命可能的不在场。
于是,不难理解他在香港和上海两重暧昧梦境里的犹疑、辗转,记忆总是充满了欺骗和悖论,悖论里埋藏着诱惑的迷人,摄影机是那只打捞残骸的船,让人物从此岸游荡到彼岸。
今年情人节,《花样年华》25周年导演特别版在院线重映,虚拟照进了现实。相爱的人必须在现实中见面,一如官方公布的宣传片里,也赫然写着“2月14日,只在影院”。提前两日的上海首映礼当天,《繁花》剧组也来到了现场,阿宝和汪小姐并肩而立,消融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边界——这是王家卫惯常使用的魔法,他喜欢让角色在不同影片间穿梭游走,制造幻觉。
他让《阿飞正传》结尾3分钟才出现的梁朝伟,空降到《花样年华》里成为周慕云,周慕云辗转反侧,又出没于《2046》的世界,苏丽珍在上述三部影片中均有登场,而《春光乍泄》里的黎耀辉与何宝荣,是片尾演职人员名单里的两位助理摄影……
与此同时,人物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各自离散,阿飞是“无脚鸟”的象征,从香港飞到菲律宾寻找生母。周慕云远赴新加坡,到柬埔寨去封存秘密,后又返回香港。苏丽珍总藏在云深不知处。《一代宗师》里的叶问和宫二,在动荡的硝烟里,分别从佛山和东北流亡至香港。黎耀辉与何宝荣自我放逐到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东邪西毒》里的欧阳锋隐居沙漠,黄药师驻留桃花岛,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共饮醉生梦死酒,以为酒精能麻痹记忆,抹去一切,可未想,往昔更加翻云覆雨,一切不过自欺欺人,一切不过如它的英文名,“Ashes of Time”,时间的灰烬……
从1988年王家卫第一部影片《旺角卡门》上映开始,到今年《花样年华》重映,一晃37年过去了。这期间,王家卫在光阴荏苒的胶片中,创造了许多“有情”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他电影宇宙中的灿烂星辰。他调度镜头的拉远和推近,在轻盈的俯瞰间,对焦人的脆弱、敏感、偏执、温存,那些溢出常规的情感模式:陌生人的邂逅、快餐店的暗恋、*手拍档间的暗潮涌动、刻骨铭心的失恋、露水情缘、同性之爱、错综复杂的爱情谜题……不带道德色彩,也无关伦理审判。
“情”被置于各种展开的、具体的生活困境中,自由流淌。人们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相遇,像植物一样生长,小动物一样心动,不假思索地爱恋。开花,结果,枯萎。他记录那些本能的颤抖、微小的颗粒,正如人与人之间情感幽微的深处,朦胧的,隽永的,无法诉说的,被误解的,永失吾爱……而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我们或许都需要一枚普鲁斯特之玛德莱德小蛋糕般的契子,让压抑的感官重新打开,追忆似水流逝的花样年华。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内外
物哀:旗袍与禁忌之爱
《花样年华》讲了一个禁忌的故事,1960年代的香港,作为邻居的周慕云和苏丽珍,发现各自的伴侣似乎有了共同的秘密,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他们开始彼此靠近,相互试探,但在不知不觉中,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秘密。
秘密因为禁忌的外衣而“不响”,两个暗生情愫的人,大雪在心中下了无数次,惊涛骇浪涌过心底都沉默。景和物皆是心境的外化,永远潮湿的街道,曲径通幽的楼梯,若即若离的侧身而过,迷蒙的街灯,屋顶低矮,走廊狭仄,红色的天鹅绒窗帘被“不知所起”的风吹荡……禁忌需要符号来表达,这符号是苏丽珍的旗袍、周慕云的西装。
人物一直在禁忌中游走,镜头中的人像总要被各式各样的“框”框住:门框、窗框、镜框……无处不在的被镜子切割的分身,和被三棱镜汇聚的他人的目光,窗棂间的铁栏杆同样分割着周慕云和苏丽珍似有若无的亲密,也重叠在苏丽珍旗袍的竖条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