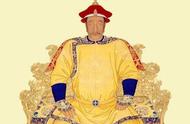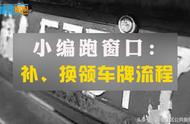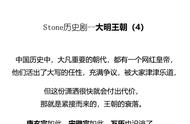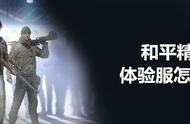在饮食上,小冰期的破坏力度是最强的。
根据史料记载:崇祯二年(公元1629 年),崇祯皇帝命官员马懋才前往陕西调查灾情,其调查结果可谓惨绝人寰。据其奏疏所写,此时因为饥荒,部分地区已经发生了易子而食的惨剧。
“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这段便是讲述了当时的陕西地区整整一年没有下雨,百姓只能靠吃草吃树皮为生,偶尔还会出现有人食人的现象。
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作物,面临着大面积减产、绝收的窘境。农民苦候一年颗粒无收,多少家破人亡,其惨烈情况难以言说,连河北区域的蒙古族、北边的女真族也深受影响。
史载“蒙古诸部大饥,多人塞乞食”,就是讲蒙古族受饥荒影响,处境艰难。
而女真族相对幸运,由于地处高纬,女真族主要以渔猎、游牧为生,本来对于严寒天气较为适应。然而小冰期的到来,气候骤降,令得大片牧草枯死,牛羊无以为食,直接令得无数底层百姓资产受损、食不果腹,却没有明朝百姓及蒙古诸部那般凄惨。
在居住上,实话实说……此时的自然环境已经十分不适宜人口居住。
据史载,小冰期时期的长江曾结冰长达一月,洞庭湖更是结冰厚达一尺。这种场景放在如今,就像是重庆的嘉陵江结冰一般,P出来都没人敢信,可当时就有这么离谱!
到了崇祯在位期间(1628—1644 年),相传曾出现过连续十年的大旱,黄河都被晒干到几乎断流,耕地颗粒无收,农民弃家而逃,很多地方空如鬼城。
而在出行上,对于底层百姓而言,这已经不叫出行,而是逃灾!

《明史·五行志》中记载,在崇祯七年八年(公元1634年、1635年),突然降下了一种可怕的瘟疫,早上发病,晚上就能死去……这场“瘟疫”,其实就是鼠疫。
古代对于瘟疫的处理方式向来十分简单粗暴,发现感染人口,*;发现感染城镇,烧!
然而北京城是皇帝居住之地,谁都没胆子在这个地方搞“消*”工作。
综合各种原因,北京城这场鼠疫绵延了好几年,后期愈演愈烈,百姓因此病亡者,高达五分之一。
最严重的时候,北京城内连路边乞讨的叫花子都一个不剩,而守卫城池的士兵更是锐减了一半,三万匹战马或病或死,只剩下一千匹堪能使用!
谁能想到,仅仅是一个鼠疫,几乎将往日人气鼎沸的北京城折磨成了一个空壳。
常言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底层百姓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没有条件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能力更没有途径,将发生的艰难情况传送到崇祯皇帝的案前。
而为了自保,他们只能铤而走险,离开故土前往异乡。
然而,此时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因为牧草、粮食短缺,索性转移矛盾、南下劫掠。逃难的百姓们先遇天灾,再遭人祸,可谓凄惨。
唯一能解救他们的明末朝廷却财政紧张、军事情况危急,对于百姓援助力有不逮,使得民间怨气更深。

天启辛酉(公元1621年),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职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
崇祯八年(1635 年),全国农民起义军已达到了 13 支,人数约 30 万。
除却民间起义军队,这时北方的后金军队,亦是纠结了大批强兵猛将,正对南方的中原土地虎视眈眈。
明朝覆亡的真相关于明朝的覆灭,大多数人都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老生常谈的角度分析,而小冰期却是一条难以被人察觉的暗线。
如著名汉学家卜正民说:“气候肯定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因素。明朝的崩溃当然不只是因为气候变化,仅仅生态环境本身解释不了任何东西。然而,当你试图去解释明朝为什么崩溃,如果不把气候考虑进去,肯定是不完整的。”
政治上,关于明朝的吏治黑暗、政治腐败,已经不用赘述。而在小冰期时期的一件事上,便可看出当时官员们的墨守成规、目光短浅。
当时蒙古诸部深受饥荒困扰,其惨烈已到了易子而食的程度。有名叫做袁应泰的官员知道此事后,曾建议收留蒙古饥民,借此收买人心,拉拢蒙古贵族,巩固两族友谊。
户部郎中却表示反对,他认为:咱们自己的麻烦事儿还没有搞定,哪里有空去管别人的事情。
而后金得知此事后,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重视。他们当时也深受饥荒困扰,却果断向蒙古诸部施以援手。
这段善缘在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得到回报,札鲁特蒙古联盟与后金交好,为后金与明朝对峙时,态度鲜明地倒向后金,为其攻打明军提供了不少助力。
而明朝则在这样的猛烈攻势下,屡屡落于下风。
军事上,当时明朝军队与后金对阵连连失利,即便有袁崇焕、吴三桂这样的名将坐镇,也难以力挽狂澜,难道只是因为小冰期吗?
抛却崇祯用兵确实不行的个人因素,这个的确跟小冰期有着微妙的联系。根据人类学家研究表明,身处高纬度的人,其身体素质和耐寒能力,要远远强于低纬度的人。
而女真族千百年来驻守苦寒之地,对于气候的适应能力明显强于明朝人。所以在入关之后,还能与持续两个世纪的小冰期“和谐相处”,靠的就是这份得天独厚的身体素质。

然而,小冰期对于女真族人不足为惧了,但大明王朝的士兵们却很难忍受“突然入冬”的温度。如《明史》所载: “明年(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镐乃会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定议,以二月十有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号大兵四十七万,期三月二日会二道关并进。天大雪,兵不前,师期泄……官兵四面围之,地泥淖,且时际穷冬,风雪裂肤,士无固志。”
可见当时的严寒气候对于士气打击有多大。
两军交战,最怕的就是水土不服导致的损兵折将。
譬如二战时期,德军百试不爽的闪击战,一到苏联就莫名失灵了。令德军万万没想到的是,踏上土地之后,最先迎接他们的不是苏联士兵的炮弹,而是从未感受过的严寒气流,令人迷惘的泥泞道路,以及宛如蜗牛般的补给速度。
这导致德军预先准备的闪电战,临时变成了攻坚战。而后苏联强大的火力覆盖和装甲洪流,更是令德军叫苦不迭,惨败而归。
某种意义上,后金与明末的对峙,也是一场因气候被迫延长的攻坚战。在这种情况下,谁的战力足、人心齐、耐力久,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无奈那个时期的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猪队友常有,而良将不常有。虽然良将,但缺乏天时、地利,也难以成事。
经济上,虽然明清小冰期被冠上了“明清”的头衔,但当时这场低温灾害的的确确是席卷了全球。
当时欧洲也是战乱不休,人口大量损失,部分国家的国力急剧衰退,外贸经济也随之下降,直接导致流入中国境内的白银数量越来越少。
而同一时期,隔水相望的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的统治,并且正在实施“闭关锁国”政策,变相隔绝了与明朝的贸易往来。
白银流入变少,银价随之上涨;谷物歉收,物价随之上涨;待物价高于税赋之后,朝廷又不得不增加赋税……明朝整体经济深受破坏。而底层百姓,面对天灾人祸,已然食不果腹;再面对这繁多的赋税,更是不堪重负。百姓无钱交税,国库空空荡荡。
没钱,一切都等于零。纵然崇祯皇帝如何绞尽脑汁,想出再多办法,也无法实施,更平息不了这大明朝的内忧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