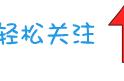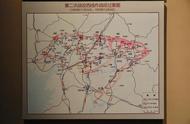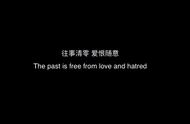文如其人。陆蠡的散文作品正是他的高尚人格和反抗精神的写照。《竹刀》里的那个年轻人,在盘剥成性的商贾逼迫的情况下,忍无可忍,一声不响地用竹片削成尖刀,并把竹刀刺进了一个吸血恶魔的胸膛,从而使吸血鬼们慑伏丧胆,使山民百姓们大长志气。当他被警吏逮捕时,他凛然不可侵犯,带着鄙夷神色,在官厅大堂上用竹刀向自己左臂刺去,以证明竹刀的能力。这个年轻英雄的气质神貌,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作家自己。几年以后,作家正是以这样的神情笑貌去向死神挑战的。陆蠡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大义凛然,痛斥敌人,保持了自己和祖国人民的尊严,这与他在作品中深情赞美和描画的青年英雄为众人的幸福而自我牺牲的悲壮精神何等相似啊!作家对英雄的赞美讴歌,完全是在一种抒情的气氛之中表现和抒写的。

陆蠡与张宛若结婚
把握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品题名为"竹刀"却迟迟不写它,反而纵笔泼墨描绘清新明丽的山野风情。也不难理解作家的匠心所在:以清新宁静、淡远静穆映衬其后的高昂激越、悲壮炽烈;以故乡可爱的山水草木对比生活于其间的受苦受难、却坚强不屈的劳苦大众;以素淡、平远、清醇的笔触渲染气氛、布置环境、设计背景,使故事带上诗情画意,让英雄染上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
倘说作家在《竹刀》里把同情、悲悯的目光投注于劳动人民的命运,并借可敬的山里青年的英雄行为表现自己的理想,寄托自己的深情,那么,《囚绿记》则是以常春藤来象征作家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追求光明的形象,从而表达自己渴求民族解放的执着的爱国主义情怀。

比较而言,《囚绿记》比《竹刀》更抽象、更富有主观色彩,它没有故事,只是记叙了作家旅居古都北平,选定有绿影的房间这样一个很小的生活细节。通过深入挖掘,作家于平淡中包藏深邃的意蕴和丰富的哲理,在常见的绿色中凝聚了一己的情感和民族的风神。也不奇怪,作家喜爱绿色,因为,"绿色是多宝贵的啊!它是生命,它是希望,它是慰安,它是快乐",它给作家以蓬勃的生命感,启发和唤醒人们去异族侵凌、祖国受辱之时,在这生生不息、向往光明的绿色面前,怎能不感慨万端、情思千缕?那被幽囚的"绿友"尖端总是朝着窗外,渐渐失去青苍的生命的颜色,"变成柔绿,变成嫩黄,枝条变成细瘦,变成娇弱,好象病了的孩子",最后,作家"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小心地把瘦黄的枝叶放回原来的位置,并"向它致诚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苍绿"。显然,作家是借这绿色的生命,借常春藤来象征自己的心境和民族的境况,歌颂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精神,抒发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一棵普通的常春藤,需要的是自由和阳光,反抗的是黑暗和束缚,由此,作家引发出悠远的思绪、感人的情致。他以蕴藉、厚实、有力的文字,真挚细腻地营构意境、抒写感情,从而强化了作品思想和艺术的感染力量。
陆蠡在《囚绿记》序里说:"我用文字的彩衣给它穿扮起来,犹如人们用美丽的衣服装扮一个灵魂。"确实,他作品中的进步的爱国爱民思想,是通过独特的美学处理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读他的作品,不仅感受到作家爱国主义感情在流动奔涌,而且在诗情画意和清词丽句中得到一种美的享受。这种美学效果,与作品把对事物的朴实而简约的叙写和深挚的哲思融为一体,与作家让自己的真情实感自然流露从而构成一种深远而浓郁的意境,均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