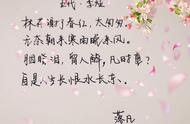已亡者:影片唯一提到孩子生父的部分是入学登记时,老师问“家长做什么职业?”,神女答,“他爸爸早就死了。”无论生父是谁、为什么没有出现,都不再重要。精神上他已经死了。
- 三类女性:被剥削者,剥削者同谋(父权制代理人)和共情者
被剥削者:就是神女。
剥削者同谋(父权制代理人):是那些辱骂、嘲笑和排斥神女的女邻居。对于这样一位可怜的单身母亲,她们毫无同情。她们所代表的女性群体,就是所谓“父权制代理人”。好处显而易见:自己从这套系统的运行中获益。
共情者:神女外出时,管家太太会帮助她照看孩子;也会对恶霸守口如瓶,拒绝透露神女迁居的新住所。她是女主角之外,全片唯一善良的女性。
三、导演如何艺术化处理“妓女”和“母亲”的身份矛盾?文艺是现实的写照。
五四运动的开启,使得女性平等问题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之后,第一次得到关注。
“出走”是逃离父权制压迫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自立。1923年,鲁迅提出“娜拉走后该怎样?”的问题,到了1934年,这项讨论进入白热化,被称为“娜拉年”。
这一年,吴永刚的《神女》上映。《神女》告诉人们,娜拉出走后有一种命运是出卖身体,这不是为她自己,是为孩子。

以女性出卖身体谋生的题材,在当时文艺作品中不鲜见,如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老舍的《月牙儿》等。
《神女》独特之处在于,让“母亲”和“妓女”两个身份共存于一个主体,通过社会和文化对这双重身份赋予的要求来展现冲突。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妓女代表着堕落放纵,母亲代表着无私纯洁,二者似乎是矛盾的。
吴永刚导演通过两个方法,解决了这对矛盾。

第一,隐晦处理涉及“性”的场景。
一个场景是,天黑时走进旅馆,天亮后走出旅馆。
还有一个场景是,神女的双脚,和一双男人的脚先后入境,停留片刻,然后向着同一个方向离开。

第二,用隐喻展现“压迫”。
章老虎用孩子威胁神女,导演设计了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章老虎分开站立的双腿,后景是神女抱着孩子,在两腿之间的画面中向上仰视他。隐喻着,这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