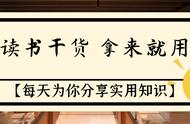2025年2月12日下午,我国著名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学者李小江逝世,享年74岁。
作为我国妇女学的学科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她在妇女研究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拓荒工作,在理论探索的同时,从事学科建设,组织课题研究,普及女性知识教育,建立相关的学术机构,集结科研队伍,主办学术会议等,成就卓越。

李小江。(图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时隔数十年,在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这位妇女研究的拓荒者却坦言,不喜欢坊间流传的“中国的西蒙娜·波伏娃”的称号,也不喜欢人们把她放到“女性主义者”的范畴当中来理解。她说她希望最后能被作为一个“作者”或“学者”被记住,“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而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在女性主义讨论声量日隆的今天,这份审慎的疏离姿态难能可贵。
这段“距离”背后有哪些考量?为什么晚年的她鲜少公开参与论辩?对于“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她又有哪些新的理解?在2024年底出版的新作《史学的性别》中,李小江系统回应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她对妇女研究未来发展的相关思考。经出版社授权,我们刊发该书的代跋,即李小江曾于2020年3月写下的文章《谈谈性别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以作纪念。
在《史学的性别》中,李小江写道:“本书最后的‘代跋’无关史学,是一个必要的背景交代。其中有两个指向史家的具体问题可能是陌生的,于女性/性别研究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一则涉及性别研究的基础理论即‘本质主义’问题,直接关乎本书的主题;二则涉及我个人的学术立场和基本观点,有助于理解我在本书中陈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多年来,海外一些后现代学者将我看作‘本质论女性主义’(Essentialist feminism)的代表,在全球化语境中给我贴上了‘市场女性主义’(the Market Feminism)的标签。20多年过去,我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没有改变,反倒是更清晰更坚定了。此文亦可看作我对海外学界的回应,放在这里,恰到好处。”
篇幅原因,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注释见原书。

《史学的性别》,李小江 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分歧”:
对待“自然”和“历史”的不同态度
李小江对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选择性引用,以及后来对中国妇女运动之独特性的论断,都建立在古典现代派文化融合的概念之上,但也对它提出了挑战 …… 清晰地回答了 20 世纪初 古典现代派和当下主义者在妇女问题的辩论中悬而未决的两个基本问题。
——季家珍《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
这两个“基本问题”,用季家珍的话说:
首先是困扰晚清时期新型女杰的两难问题:是接受还是拒绝“妇女”身份。……致力于研究女性的独特身份。她不畏所谓本质主义的指责,甚至因为担心女性问题的特殊性而拒绝“性别研究”这一概念……李小江比20世纪初的女作家更公开地关注女性的身体存在,她也较少受到女性身份和国民身份双重责任的困扰。她的事业是毫不含糊的女性事业。
难得她将“身体”看做首要的基本问题,更难得的是她对所谓“本质主义”的准确描述,海内海外,这是唯一。因此,她对第二个基本问题即“全球化”与“国家差异”的表述也很到位:
李小江像她的古典现代派前辈,而不像她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同龄人,她并不反对全球化……虽然她认为妇女问题从本质上说是普世的,但她也认为国家差异就像性别差异一样深 刻。因此她细心地区分了中国和西方女权运动产生的历史政治背景,并在语言上谨慎地对待这些差异……她认为“封建历史” 是嵌入在国情中的“珍贵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力量。她承认,与这段历史失去联系就意味着失去我们自己。
正是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季家珍道出了我与西方女权主义在理论和立场上的根本分歧。同时,她也认为:“1995 年在北京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的代表们承认,李小江所强调的中国和西方经验的差异使西方女权主义的国际霸权地位面临挑战。”挑战,其实是双向的。对中国的一统天下,女性主义的介入本身就是挑战;同样,对妇女研究领域中女性主义一统天下,“发出中国妇女的声音”也是挑战,因为它明显地有别于西方的声音。只是我和我的那些海外朋友们都没有料到,我们这些以不同方式“毫不含糊”地投身于“女性事业”的同路人,在学术研究领域分道扬镳;分歧就在对“女性人”的质的认识, 因此导引出了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
西方世界,性别认知以《圣经》为平台,夏娃由亚当而生,“女人—第二性”的说法有它难以撼动的神学基础。《第二性》出自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 The second sex(1949)。20世纪80年代我向国内推介女性主义,就是从翻译《第二性》开始的——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与feminism保持距离,基于一个不能忽视的认识论问题:生为女人,我们该如何认识自己天赋的身体以及人类历史构建生成的性别差异?汤尼·白露的书中强调李小江与波伏瓦在理论上的相似性以证明女性主义的普世性;可是,在回应文章里,我谈的是分歧:
我和波伏瓦最重要的分歧,就在对待“自然”和“历史”的不同态度。因此,波伏瓦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生成的”,我只能认同一半。在我看,女人(women)的确是后天生成的,女性(female)却是天生的。我不认为女人成为“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全然是男性意志主导的结果,而宁可看它是人类历史进化中一个必然的阶段。在我这里,“天生” 和“生成”不是二元对立关系。我认为,只有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客观地认识历史,女人(男人也一样)才可能在有限的选择中有效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和人生。

《夏娃的探索》,李小江 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第二性”的说辞在基督教世界生根,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与女性主义的传播是同步的。女权运动的兴起与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的平等诉求同期同步,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石,恰恰是西方世界中以启蒙为核心的现代主义运动,源远流长,长达3个多世纪。借助西方话语和西方中心价值体系主导世界百年有余,女性主义因此有其雄厚的学术资本。
何谓“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
今天,女权运动成果丰硕,妇女解放已然从根底上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但是在全球范围里,今天妇女获得的解放并不都是女权运动的成果,绝大多数女性人口的所属地域 也不在西方世界。与非西方的女性直接相关的种族、阶级、文化差异和民族问题,很长时间里都是女性主义的盲区;但是却不乏盲区中的追随者——为什么?就因为“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在“女性”(female)名下可以让全世界的女人结成性别统一战线——吊诡:女性主义者极端反对“女性本质主义”坚守的自然属性(sex),实则恰恰是feminism难以撼动的理论基石——遗憾的是,女性主义学者对此大多认识不足,任由世事变迁学路更新,狭窄的学术视野和单一的性别立场始终没有得到必要的调整。
具体到以西语或西学为根底的中国女性学人,对主流话语的追随和对西方理论的盲从合二而一,在学术根基上有三个难以弥补的缺陷:一是对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认识不足,概念先行成为通病;二是对所学专业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一头钻进女性主义视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难堪的,是对本土即中国历史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理解,对近代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进程漠然不知,迷失方向在所难免。
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不同于西方女权运动,是因为中国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早已建构起了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性别制度,性别观念判然有别:“阴/阳”互为本体相依而存,男女在本质上不是从属关系。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女性价值体现在各种“关系”中,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第二性/女性”。
我在很多地方谈到:历史中国,没有女权;有母权,也有妻权;无论母权还是妻权,都在君主体制和华夷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朝政中,君妻君母之作用不可小觑;家族关系中,《红楼梦》里贾母的尊位并非虚言,在现实生活中有其原型基础……对中西之间性别制度上的种种差异,谙熟中国历史的李约瑟博士看得很清楚,在多种场合以及在传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他一再提到:“信奉《圣经》的各国人民,以及一般说来是西方,一贯过分习惯于男性统治……对中国人来说,至善总存在于阴和阳,即宇宙间女性与男性力量的最完美平衡中。”二元对立,导致人世间较多的*戮和奴役;“征服”不仅是政治理念,也是西方民族倡导的生存手段。二元对应的观念,有助于创造一个和谐共生的世界;“和合”不仅是处世之道,也是当权者的执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