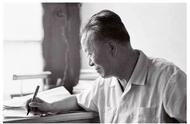另外,“为诗歌而生”这一特点也体现出了当时西方在文学途径上寻求社会出路的观点,即“文学原始主义”,看重诗歌这一“发自肺腑,不加修饰”的文学体裁,认为“回归原始”,才能回归初心,重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这一特征也为之后李白逐步成为西方人眼中中国诗歌的代表以及“天人合一”理念的最好诠释作了铺垫。
文学家:强调“政治启蒙”——主流认识约翰·司各特所作长诗《东方牧歌之三:李白,或一个好官——中国牧歌》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文学家创作。诗歌一开始罗列了很多中国的地名,比如河南、江西、西湖等,而李白作为一个官员,他管辖的地方就在这些山川河流之际。

作者对李白身份及形象的描述与我们的认知有较大的差别,李白被描述为一个王子、一个总督、一个温和的统治者、一个忧郁的主人公,他为往昔朝会之时的匆忙懒惰而惋惜,为自己曾经的不公之举而懊悔,他哀叹一切努力徒劳无果,终不能释然。
虽有歌女奴仆环绕四周,为他吹笛弹唱,歌尽古老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千古帝王、有情之人,以慰其忧愁之思,但李白却始终得不到灵魂上的快乐。

他再次追忆往昔,担心自己既未承父辈之荫德,又不及百姓之重托,“在愁绪中他忆起了昨夜之梦,他梦见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美丽世界,在这里‘孔教’的‘牧师’给他带来了平静。
诗中的李白拥有权力与财富,但得不到灵魂上的快乐,“孔教”的“牧师”(孔子)给他带来了平静,诗人将孔夫子视为了一个和耶稣相似的形象,儒教也是像基督教一样的宗教,儒家思想代表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哲学家、启蒙者的形象出现。

司各特在诗前的注解中说,他创作这首诗主要是受到传教士杜赫德的影响,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杜赫德将孔子与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相比,认为他“胜过了这三位先哲”,且“达到了人类智慧的极点”。
而历来耶稣会士笔下的孔子形象也都大致相同:孔子是现世的人,不是神;孔子是伟大的哲人和教育家;孔子道德完美,给后人提供了道德指南;孔子恢复风俗,倡导原初的宗教,尊崇全知全能的“天”。
这些对于孔子形象以及“儒教”的阐述,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法国人在寻找一种新的道德,“在伏尔泰的宗教观里,比‘尊崇上帝’更重要的原则,是‘注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