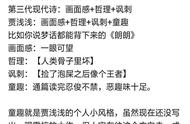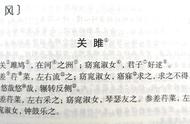李培禹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正逢抒情的时代。时代的濡染,让李培禹自然而然地经历了一个“读诗·品诗·写诗”的诗歌之旅。于是,对诗歌的亲和,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化为他的精神细胞。率然吟咏成为他的生命常态,他甘愿成为生活的歌手和时代的歌手。
德国哲学家齐美尔说:“生命并非完全是社会性的。”弗洛伊德也把人的心灵划为意识与潜意识。他们都强调“非社会性”的东西,主张逃离“理性”“良知”和“社会责任”。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则把他们的主张变成诗论,特别宣称:“诗不是表现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他所说的“逃避感情”,不仅指现实感情,当然也包括社会感情,因而整体地内趋,把表达私人话语凌驾于公共话语之上。进入新的世纪,中国诗坛在对现代主义的追逐中,很多诗人以“逃避”为上,以书写“私人话语”为宗,诗作极端个人化。然而李培禹却绝不闻风而动,他坚信,“民歌是诗歌之母”,客观性、现实性、时代性、人民性和社会性是诗歌的基点和本源,也是诗歌创作的大道通途。
因而他在物象(河山和星辰)、世象(人群和社会)、心象(感情和感悟)这三个维度上觅诗。这就使他的诗歌创作,取材广泛,形式多样,情思纷繁,好像无处不诗、无时不诗——他率性撷取,神采飞扬,快乐地歌唱。一切都承继着《诗经》的传统,大地、人文和心灵交汇融合,高奏“复调”,尽情地赋比兴、风雅颂。这样的风格,在他的诗集《失去》(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中得以充分体现。
譬如《和长城握手》,“风中我站在金山岭的垛口/思想感情的波涛在放纵奔流/长城啊,此时我抚着你每一块岩石/知道吗?我是在和你紧紧握手//用不着山谷录下豪迈的誓言/握手,十指连着心头/心中既已燃起振兴中华的烈焰/攀登吧,我所有无愧于长城的朋友”。可以看出,在诗人笔下,长城既是物也是人,既是历史也是时代,既是客观存在也是主观情感,有着“复合”的品质。所以,当有人说,李培禹的诗有些直白和清浅,我不禁摇头,认为这正是他在深处思考之后,厘清了人情事理,获得了明晰的认知,便自信地进行深入浅出的表达。一如结晶的过程,中间之物往往混沌一团,貌似深奥与神秘,到了最后反而晶莹剔透。换言之,这是他自主性的追求,反拨着现代主义的所谓孤冷与玄奥。他写入世之诗,照拂人间情感,观照现实人生。
他的写作取向,注定了他的诗思与山河同在、与时代同脉、与生活同轨、与人生同感。这就不难理解,他当年小小年纪,就勇于与贺敬之、臧克家那样诗歌大家唱和,写出《雷锋和我们同在》的长歌;也不难理解,遍染风尘之后,他还保有一颗湖水一般清澈的童心,在沧桑处抒纯美之情。
譬如《赛里木湖的波光》,“赛里木湖的波光/在哈萨克小伙的心中荡漾/他们世代弹着冬不拉/湖水便像圣泉一样清凉……/赛里木湖的波光/把锡伯族猎手的眼睛擦亮/他们封存了骑射的弓箭/家乡更有了满坡满岭的牛羊……/今天,赛里木湖美丽的波光/让我这个远方诗人的心儿滚烫/她一定接纳了我笨拙的诗句/不信你看,湖水正涌起一层层波浪”。
从哈萨克小伙到锡伯族猎手,最后到“我”,从远方到身边,一路清澈,情感就有了普遍性。这样的意象,正是人间性所在,像阳光普照,豁然地有了明媚的力量。这正暗合了浪漫主义的底色,其核心词是: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
李培禹的诗集名为《失去》,读罢掩卷,却内心盈满,有始终“得到”的感觉。他忘情地做着时代的歌者、生活的歌者,一路吟唱,大在小处、诗在凡处,让人心中激荡起感恩之情,由衷地感叹:有诗的日子真好,有诗的日子很年轻!
(作者:凸凹,系北京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