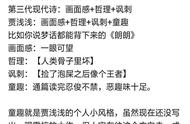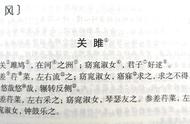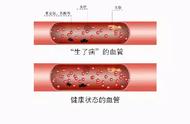做不出文章是肚子里没有文章,做不出诗来是不是肚子里没有这个诗呢?为什么要做文章?有话不得不说。这个“不得不”很讲究,因此做文章不光是肚子里的事;那做诗“不得不”就更加重要了,否则不如不做。不像是个诗的年代,却忽然纷纷谈起诗来,好像有些奇怪。
“现代诗”回避“宏大叙事”,终于到了社会对诗和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你那些津津有味搞进诗里的东西谁愿意看啊?你自己都未必有兴趣,只是你极少一些人至今还不可告人地保留着写诗的习惯,把一些鸡零狗碎凑进你那“诗”里,终于寂寞到了极点,想吸引些读者围观,所以在你那“诗”里搞进些可怕的新鲜事物诱惑人,这就是“现代诗”小股土匪作案的伎俩。
老子曰:“将欲取之,必姑予之。”这不是阴谋,这是常识。诗歌流落到捡破烂的境地,完全是咎由自取。当初自以为是大鸟,以承担社会责任为耻,以描摹私密意识为乐,彭子曰:“崽卖爷田心不疼!”白话诗人们把新文化运动积蓄下来的祖产典卖一空,人类社会还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这样不需要诗歌!
曰:“会心处当不在远。”随时随地都可能引起诗人的咏叹。中国有称“诗国”,有诗的传统。虽然这个时代,做诗似乎是弱者的行为,正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但历史上相似的时代并不少啊,什么时候像现在这么“绝望”过?是“现代诗”搞坏了社会的胃口,无论作者与读者对诗这东西都不肯再有期待。
没了诗,社会就失去了感动。都说诗人很敏感,神经质,这东西存在社会可以不麻木。我觉得朝廷也应该对此有认识,从社会学角度看待诗和诗人的作用。感动不重要吗?民气不重要吗?人心不重要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牺牲了感动,问题会很大。国家战胜“公知”,靠的是人心和民气;西方地怪主义忽视了中国底层的向背,以为“公知”可以代表中国人民。但这种底层的民气和人心,来自于“感动”的历史积累,它是消耗性资源,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关于诗歌,我主张取消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分行”形式,强制性彻底解决“分行散文”的讽刺性历史遗留问题,依靠口语白话的内在韵律——内在音乐性与“散文诗”等其它文体相区别。
那是语言文字形式上的,更加内在的形式上,我主张“由最具表现力的本质特征性细节,为感动自己和别人构造成一种意境形象,熔铸在看似脱口而出的三言两语之中”,从短诗、极短诗、“一句话”的诗开始恢复诗歌文体的内在美学品质。要把“一句话”的诗作为白话新诗的基础训练,用来洗炼口语白话,呈现口语白话的可观之美。
现在说“感动”,感动自己,感动别人,在诗歌创作中是要用语言文字达到这种效果;但“感动”应该是客观的,是被感动的诗人用艺术创造再现这种“感动”。所以才有“最具表现力的本质特征性细节”之说,那都来自于“感动”你的客观事物。
“感动”就是我开始说的“不得不”,它来自于随时随地的遭遇,“小确幸”之喜也可能感动你,“宏大叙事”不可回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忧郁”被称作“诗人气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但诗人的忧郁肯定是大丈夫的忧郁,“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这是从客观方面说到主观方面,不同的主观会因不同的客观而“感动”,而且你还想再去“感动”别人,那你最好去做一个社会性的人,一个有意识的社会性的人。因为任何人本来都是社会性的,但那样你还仅仅是个“客体”,自觉而有意识的人才是“主体”,然后才可以做“诗人”。现在的社会之所以不需要诗和诗人,就是因为现在的诗人并没有社会主体性,而只有个人主观性。
“感动”是客观的,因此“诗兴”是不可预期的,“为赋新词强说愁”是没有人愿意阅读与欣赏的。风雅颂,赋比兴,这个“兴”是“诗兴”,但“赋比兴”并列,似应读“兴起”之兴——这样也不清楚,不是“一时兴起”之兴,而是“兴起风潮”之兴,阴平之声。
“赋诗一首”,需要“诗兴”,这是“一时之兴”,过期不候,应该抓紧时间,寻找“感动”你的客体“最具表现力的本质特征性细节”,把诗“赋”出来,捕捉细节,便是“赋比兴”之“赋”法;难以捕捉,难以把握,则比较其类似事物,大致予以表现,此是“赋比兴”之“比”法。
生动白描,是赋法;奇幻喻象,是比法。所谓“朦胧诗”,追求“意象”,其实是比法。唐诗李商隐,也是因比法而朦胧。比法能给人特殊美感,其实也可能是因无法捕捉那种“最具表现力的本质特征性细节”仓促造成的,当然也可能是有意造成的,专为取得这种特殊效果。
“朦胧诗”追求的“意象”,跟“意境”是两回事。诗歌文学形象不同于小说、戏剧,诗歌讲究“意境”,而不是人物性格,但诗歌是“元文学”、“元艺术”(“美学”在西方也曾叫“诗学”)所以现在的小说和戏剧也有深度追求“意境”的。“意境”是诗歌提供的文学形象所产生的一种“境界”感,说白了就是能让你“感动”的那种东西。而“意象”就是比喻性的假借形象或假借事物了。
“赋比兴”之“兴”,应该读阴平声,动词,跟读去声的“诗兴”其实大有关系。曰:“先咏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也。”其实瞎扯,你把这“他物”删简掉,诗味必然大减,其中另有神秘关系。这“他物”就是“诗兴”之所由来,诗人一时搞不清楚,也就是一时难以捕捉到那个“最具表现力的本质特征性细节”,便把那个客体草草捆绑来撂在全诗的最前面。一切都与神秘的“感动”有关。
生活中“感动”你的事物,不要轻易放过,即便你并不想做诗人,也不会去作诗作曲。对了,诗歌的音乐性应该是与生俱来的,纯音乐都是从诗歌分离出来、发展起来的,尽管后来纯音乐发展到能使语言依附它成为歌词,尽管歌词大多丧失了诗歌许多固有的美学品质;这样取消白话新诗的“分行”形式,按一般文字形式加上标点符号书写印刷,它这种内在音乐性依然可以跟散文诗等其它文体明显区别开来。只要控制它不要僵化地形成“格律”,而只按口语白话内在的自然韵律获得那种音乐性,就好。
回到“感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保持能够“感动”的健康状态,才会形成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