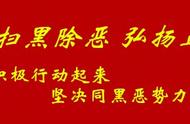学校对面,比学校海拔略高十几米的山梁上,是个土地庙,从学校步行前往,不到五分钟即可到达。当地的老人说,五几年刚建校时,没有校舍,就在庙里办起了学堂,坚持了好多年。这么算来,土地庙竟然是学校的前身,土地爷也算是为当地办了件实事。而最初的几任老师与当地的土地爷朝夕相处,不知道是不是也沾了些仙气?当然,这个就不好考证了。而九年后,在我彻底离开学校后的那年夏天,镇上的暑教会上,我作为“优秀班主任”代表在会上发言,开头我就说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的旁边有座学校……一时之间,众人叹惋,论作笑谈。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不知道那时能以轻松略带调侃的态度去面对它,是否与我已经彻底脱离了它,跳出了它,以一个旁观者而非参与者的角度去回望它有关。而当时的我必定不是现在的我,现在的我只是如同置身事外一样地看着当时的我,就像在看一场已经散场的电影。而今,艰难被回忆起来,竟多成温暖。这也许是我们人类对抗磨难的优秀特质,也就是所谓的“忆苦思甜”吧。
回到当时,那是我任教的第二年,一个不到二十岁的男性青年教师,和一个孤独闭塞的学校,即将开始一段长达九年的奇妙之缘。于是,在一个毫无防备的秋日,父亲带着我,来到这里。
远远望去,学校的门口聚集了好多人,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入学的。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家也算是教师世家了。因此,在父亲的指导下,我们就着教室里的桌椅,很快就办理完成了入学手续。由于第二天才正式开学,孩子和家长们都四散离去,空旷的校园重回幽静。秋风轻起,整个暑假无人问津的操场,各路野草摇曳着,似乎用炫丽的舞蹈在迎接它新的主人。是的,毫无疑问,接下来,我将是它的主宰。

于是,父亲和我开始收拾我的寝室和厨房。寝室和教室是连在一起的,教室占地两间,寝室占地一间。教室是一个大通间,而寝室恰恰相反,一分为二,一间窗户临着后面的溪谷,一间窗户面朝操场(若是能面朝大海,那是最好不过了)。我将床安在了朝向操场的那间房里,这样我可以随时通过窗户观察操场,达到一种“统揽全局”的错觉。寝室简单到了极致,两条板凳架上三块木板,形成了我的床。靠窗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平日里工作读书。靠墙一张略小点的桌子,则是堆放一些生活用品。
九年里,我就是在这样的寝室里亦工亦宿,“运筹帷幄”。厨房设在对面,学校的后门旁边。一个硕大的土灶横亘其中,却不显得突兀。两口大小不一的黑锅,彼此煮着春秋。简单洗涮后,父亲开始烧火做饭,娴熟地下面、捞面、炒面,锅铲上下翻飞,我则在旁边默默观看学习。这是我在留驾沟的第一顿饭,厨房很黑,炒面很香。而后来,我在留驾沟做得最多的饭也是炒面,吃多了炒面,自然就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