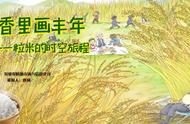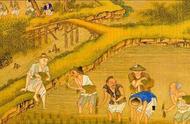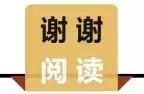言归正传,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世界仅有的几个植物驯化中心之一,在蔬菜种植历史方面不是一般的悠久。再比如传播速度。在世界最初形成几大植物驯化中心的过程中,跟中国几乎处于同一纬度的新月沃地帮了不少忙。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白天的长度和季节变化几乎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在雨量、植物疾病、植被类型等方面也极为相似,这对于作物的传播极为有利。
历史经验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种植技术以每年0.7英里的速度从新月沃地向西传入欧洲和埃及,向东传入印度河河谷。而相比之下,在纬度差异较大的美洲,传播速度就慢很多了,玉米和豆类仅仅以每年0.3英里的速度向墨西哥北传播。这就使得来自新月沃地的蔬菜品种,能够跟中国本地的自然条件无缝衔接,也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古人们毫无顾忌地引进了大量来自新月沃地的植物。比如汉代出使西域的张骞,引进了一大堆蔬菜瓜果,带来的种子,包括但不限于芹菜、香菜、蚕豆、黄瓜,还有大蒜,几乎够打一局《植物大战僵尸》。
可见,无论是蔬菜培育还是引进,中国都占尽了机会!
中国人不得不种菜
中国人种菜技能的养成,也伴随着无数的无奈和叹息。在漫长的封建历史进程中,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占有量也不断减少。在农业生产力提高极为缓慢的前提下,中国人能填饱肚子已经很不错了,更遑论吃肉。
单从技术层面来说就不可行,因为吃肉付出的代价简直太大:每次某种动物在吃某种植物或者另一种植物时,食物生物量转化为取食者生物量的效率仅为10%左右,这也就是说,要花费1万斤左右的饲料才能喂养成一头1000斤重的牛(数据出自《枪炮、病菌与钢铁》)。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中国古代,能吃上肉的,也仅仅是极少数人而已。不光限购,更是要特供。如《礼记》规定,天子才能吃牛肉,诸侯平常吃羊肉,每月初一才能吃一次牛肉,大夫平常吃猪肉和狗肉,老百姓也就是能吃点鱼肉,“鱼肉百姓”据传由此而来。对于百姓吃肉,孟子支过招,号召大家“养鸡豚狗彘之畜”,并且要做到“无失其时”,这样的话,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上肉了。对吃不上肉的人来说,吃肉的人是可耻的,天天吃肉的人是可恨的。商纣王“酒池肉林”自然是招人厌恶。
国难当头,曹刿准备给君王出谋划策,老乡们也一肚子意见:“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意思就是人家吃肉的人商量事,你这个吃素菜的掺和什么?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遇到战乱和灾荒,甚至连粮食和蔬菜都吃不到,《尔雅•释天》有言,“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饥馑”一词由此而来。也就是说,无论是粮食招灾,还是蔬菜匮乏,都让人很难受。
19世纪游历中国,并对中国国情有深入研究的英国人乔治•斯当东,就灾荒问题做过一个精辟评论:“在中国一个省份内发生饥荒次数超过一个欧洲国家。”在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中,“我”和姥娘有这样一段对话:“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哪一年?”姥娘生于1900年,她对“1942”这个年份的忘却,不是因为这一年的大饥荒不触目惊心,而是在她老人家经历的日子里,饿死人的事确实发生得太频繁了。

有专家统计过,从周朝到1937年,中国总计发生过5258次饥荒,而欧洲在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饥荒次数为864次。对于灾荒和饥饿的记忆,使得“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成了中国人的基本诉求。于是,中国人总是不遗余力地开发每一寸土地,栽种上能填饱肚子的粮食和蔬菜。
相对于一年只能熟1~2次,最多3次的粮食而言,蔬菜的生长周期很短,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可以收获得更多。而且,种蔬菜更具有灵活性,可以随意选择适合这个季节栽种的蔬菜,比如大白菜在4月—10月都可栽种,南瓜2月—10月都可栽种,萝卜3月—10月都可栽种……这些蔬菜对于生长地要求也不高,区域不大的房前屋后就足够。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粮食生产逐年攀高,饥饿开始逐渐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在历经40年的稳定、快速发展后,新一代中国人几乎没有太深刻的饥饿记忆。但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仍然会存有长期饥饿形成的忧患意识——“在我们家,绝对不能对外婆说因为不饿就不吃饭了这样的话,这对她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而且每次饭后,她总会吃光我们剩下的饭菜。”“外婆经常说,人只有吃饱了才踏实,才会有安全感。”“守着粮食,种上菜,心里才踏实。”
当然,在漫长的被迫种菜的历史中,中国人也渐渐形成了吃“草”的文化,把素菜做得有滋有味就成了一种本能。《西游记》第一百回就列出了一个素菜单:“烂煮蔓菁,糖浇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添来姜辣笋,数番办上蜜调葵。面筋椿树叶,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干薇。花椒煮莱菔,芥末拌瓜丝。”这些纷繁食材的错综变化,是令中国素菜出神入化的根基,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部分。
种菜包含着中国人的精神诉求
在中国,种菜从来不是“下等人”的事,皇亲贵族和知识分子也都很喜欢种菜。古代天子每年都会“亲耕”。这项具有强烈仪式感的传统起源于汉文帝,之后,很多皇帝都会在每年正月下地劳动一番,以示对“三农”的重视和尊重,给全天下的农人们加油打气,同时也许下愿望,祈祷一年的好收成。
后来,“亲耕”也逐渐有了一套繁杂的礼仪,表演的成分更加浓烈,套路化痕迹更明显。到了明清两代,祭农活动达到顶峰时期,祭祀亲耕制度周密详备,整个仪式隆重有序。从保存的清雍正帝先农坛亲祭图、亲耕图和有关典籍上,可窥一二。皇帝竟然也种田,这让外国人大为惊诧,享誉世界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曾在《论孔子的学说》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
知识分子和贵族也种菜,他们崇尚田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为“耕”与“读”相结合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还把“耕读传家”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勤奋“耕读”的农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实现从农人到官僚的切换,走上人生巅峰。
同样,经历宦海沉浮,对官场心灰意懒的官僚也把田园当成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完成从官僚到农人的切换。《三国演义》中,刘备甚至通过种菜来掩蔽自己的锋芒和英雄本色,减轻曹操对自己的怀疑,“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即便是世袭罔替的贵族子弟,有时也把种菜当成一种乐趣。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贾府为元妃省亲而建,典型的豪门院落。为了不让偌大的院子空着,元妃便让家里的姐妹及宝玉入住大观园。
没想到,这样富丽奢华的院子里竟被这些贵族子弟种满了菜!“……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漫然无际。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时一见,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

贾政作为工部员外郎是有官职的,见到大观园里的菜地,都生发了归农种田的想法。当然,贾政毕竟是中年之人,上了岁数,所以想到种田也算是正常的。但是,作为大观园里的贵族子弟们,却也能在闲散之余种种菜,足以说明中国人对种菜就没有什么抵触心理,也不会认为种菜是一种低贱的活动。军队也种菜,自给自足。
中国军事自古以屯田闻名。屯田就是让士兵耕种田地,说白了就是军队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种蔬菜,进而自给自足,无须国家财政支持。这与西方军事远征大有区别。今天贵州屯堡文化就是明朝军垦屯兵遗迹。李牧雁门关屯田,诸葛亮屯田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屯垦戍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等,这是重农经济的军事特点。
如此看来,在中国,种菜不但不会被歧视,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情操的陶冶、精神的追求,甚至是一种低调的表现,这在把种田之人看作农奴的古代西方世界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在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糅合下,种菜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一项属性。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说,每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